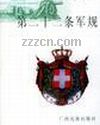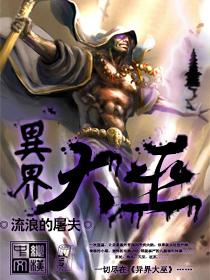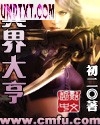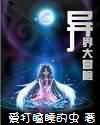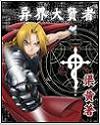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一卷 风云紧急-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他的主要僚属之一,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负一份责任。在这五年期间,国内的复兴有了可观的成绩。这个政府是一个沉着而又干练的政府,在此时期内,逐年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恢复。在政纲方面,虽然不能吹嘘说有什么惊人的或引起争论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无论根据经济的或财政的标准来衡量,人民大众的生活确见改善了。在我们任期终了之时,国内和世界的景况,比起我们就任之初来要舒适和富饶得多。这是一句平凡的、但也是很实在的评论。
在整个欧洲,政府获得了好名声。
※※※
这时兴登堡在德国上台掌权。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战败后的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于1925年2月底去世。现在全国必须选举一个新总统。所有的德国人过去一向是在家长式的专制政治之下长大,并受到言论自由和议会反对派这种影响深远的习惯的调节。失败的战神张着羽毛脱落的翅膀,给德国人带来了极端的民主体制和各种自由权利。但德国所经历的一切使全国四分五裂,彷徨而无所适从。
各党各派互争雄长,争权夺利。在一片混乱之中,出现了转向兴登堡元帅的强烈愿望。兴登堡这时已退休家园,但仍受人们爱戴。他仍旧忠于流亡国外的皇帝,赞成〃按照英国的样板〃恢复帝制。这自然是最合理、但又最不投合时好之举。
当他被提名为在魏玛宪法下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三地说:〃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然而,请他出山的压力继续存在,最后找到了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去说服他,才使他不再犹豫,放弃他的本意而为国家负起责任。对于为国尽职,则是兴登堡向来勇于承担的。兴登堡的竞选对手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马克斯和共产党的台尔曼。4月26日,星期日,德国举行选举。投票结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兴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六十六票;
马克斯,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十五票;台尔曼,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一票。兴登堡声名显赫,这次竞选又出于多方劝说才勉强答应,与各方利益又无牵连,在竞选者之中占了上风,结果以不及一百万的多数获选,在全部票数中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多数。当他的儿子奥斯卡尔在早上七点钟把他叫醒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把儿子骂了一顿:〃你为什么要早一个钟头叫醒我?就是到了八点钟,事情也会是一样的呀!〃说完又去睡觉了,直到平常要叫醒他起床的时间才起床。
兴登堡的当选,在法国一开始就被视为德国的新挑战。英国方面的反应则比较平稳。我一向希望看见德国恢复它的荣誉和自尊心,让战争带来的仇恨心归于消失。所以这个消息根本没有使我感到焦虑。劳合·乔治在我们再次见面时对我说:〃他是一个极通情达理的老人。〃的确,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废物也总比一个暴君好些。〃①不过,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几乎没有人会预料他能再度连任。他在各个政党之间尽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总统任期内的确给予德国以一种并不威胁其邻国的稳重的力量和安宁。
①引自特奥多尔·勒辛(1933年9月被纳粹暗杀)。
※※※
192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当时法国总理赫里欧提出一个建议。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声明,如果在莱茵河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能签订一个以美国政府为保证人的公约,规定在一个长时期内承担不对订约国发动战争的庄严义务,则德国愿意宣布接受。此外德国也可以接受一个保证莱茵河区疆界现状的公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法国政府着手同它的盟国磋商。在英国方面,奥斯汀·张伯伦于3月5日在下院公布这项消息。由于法国和德国出现国会危机,延缓了谈判的进行,但经过伦敦与巴黎之间的协商后,在1925年6月16日由法国驻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提出一个正式的照会。照会宣称,除非以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先决条件,否则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德国不得提出修改和约条件的任何提议。比利时应列入订约国之内;最后,应订立一个法德仲裁条约,作为莱茵兰公约的当然补充。
6月24日,英国下院就英国应采取什么态度举行辩论。
张伯伦先生说明,按公约规定,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西欧。法国也许要确定它同波兰和捷克的特殊关系,但英国将不承担在国际联盟盟约明确规定之外的任何义务。各自治领对西欧公约并不热心。史末资将军希望避免区域性协定,加拿大态度冷淡,只有新西兰准备无条件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但我们仍然坚持。在我看来,解决法、德两国千年来的冲突,似乎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如果我们能把高卢及条顿两大民族,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促成密切的团结,以防止发生新的纠纷,而实现共同的繁荣和相互的依赖,使过去的对立消失,则欧洲即可再度兴旺起来。在我看来,英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在于调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纷争,此外似乎没有其他利益可以与此相比或与此相抵触的。直至今日,我的见解仍然是如此。
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提出了为各党所尊重的见解,内阁一致对他给予支持。德国在七月间对法国的照会提出答复,接受把西欧公约和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两件事结合起来,但说明关于普遍裁减军备的问题有先行成立协议的必要。
白里安先生来到英国,就西欧公约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八月间,法国取得英国的完全同意,正式答复德国。德国必须无条件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必要的第一步。
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这就是说,和约的规定,除非或直到经过互相同意而加以修正,将继续有效;德国也没有得到协约国裁减军备的具体保证。此外,德国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压力和激情之下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如要求取消和约中关于战争罪责的条款,要求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暂不解决,要求协约国军队立即自科隆撤退等,德国政府都没有十分坚持,但即使坚持,协约国也不会答应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洛迦诺会议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在光坦如镜的湖水旁边,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
会议的成就是:第一,五国订立了相互保证条约;第二,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仲裁条约;第三,法国和波兰、法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专门的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并接着发生无理的军事行动时,法国保证援助波兰和捷克两国。这样,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一致反对任何订约国破坏协定,对兄弟国发动侵略。英国向法、德两国提出庄严的保证:如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对象,则对该国给予援助。这种影响深远的军事义务获得了议会的承认和全国的热烈支持。这样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至于英国或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至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作为财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些问题。我对于这种两个方面的保证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国保持军备,而德国废除军备,则德国当无进攻法国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国进攻德国,这就会自然而然地使英国成为德国的盟国,这样法国就绝不会进攻德国。这个建议,在理论上似乎有危险如德、法之间发生战争,我们就得保证加入这方或那方但是像这样的一场灾祸实际上是很难遇到的;这反而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对于法国裁减军备和德国重新武装,向来都表示反对,因为这会立刻给英国带来更大得多的危险。在另一方面,英国和国际联盟(根据协定德国已加入国际联盟),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种确实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基本上居于公证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们希望这种平衡局面能维持二十年,在此时期内,在长期和平、信任增长和财政负担的种种影响之下,协约国的军备也将逐渐缩减。显而易见,德国的实力一旦和法国大致相等,危险就会出现,更不用说德国变得比法国更强大了,但所有这些情况都似乎因有庄严的条约义务而被排除。
洛迦诺公约只涉及西欧的和平,因而希望继之有一个所谓〃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如果能够以防止德法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样精神和措施来控制住德俄之间未来战争的危险,那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了。但即使是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也不愿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规定。苏俄处在由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所组成的〃防疫线〃的后面,在孤立的状态中盘算着。虽然我们继续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对于使德国在东部边界上得到较大的满足的企图从未置若罔闻。但在这短短的有希望的几年中,始终没有碰到好机会。
※※※
人们对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所产生的条约都热烈欢迎。
鲍德温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因为没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同施特雷泽曼亲密、友善地共进午餐。我们在极其友善的气氛中聚会,并且一致认为,如果欧洲最大的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又自感到获得了安全,则欧洲的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获得议会真诚的同意以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获得了嘉德勋章和诺贝尔和平奖金。他的成功就是欧洲复兴的满潮标记,从此便开始了和平复兴的三个年头。尽管旧有的敌对只是处在睡眠状态中,新兵击鼓之声已隐约可闻,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根据确实得到的基础,我们将打通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
在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欧洲风平浪静,不仅为过去二十年所没有,而且在此后至少二十年中也没有。自从我们缔结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对德国有一种友善的情感,法国的军队和协约国派遣军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加入了不完整的国际联盟。在美、英贷款的体贴入微的帮助之下,德国很快就复兴起来。它新建的远洋轮船获得了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荣誉称号。它的贸易有飞跃的发展,国内情况十分繁荣。在欧洲,法国和它的同盟体制也似乎安然无恙。凡尔赛和约关于废除军备的条款也没有遭到公开的破坏。德国的海军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空军在禁止之列,并尚未再起。在德国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至少为了慎重起见,强烈反对进行战争,而德国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相信协约国会容许他们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却展开了我在下面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但对此有所察觉者,却只限于寥寥可数的一些财政界人士;而且他们看到前途太严重,也吓得噤若寒蝉。
※※※
1929年5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党较之保守党只占微弱的多数。约有六十席的自由党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很明显,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之下,自由党一定会对保守党采取敌对的立场,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我和鲍德温完全同意:我们不应以一个少数党的地位或依赖自由党的靠不住的支持来组织政府。因此,虽然内阁和党内对应采取的方针有些意见分歧,鲍德温还是向国王提出了辞呈。
我们全体乘专车到温莎,缴奉印绶,正式辞职;六月七日,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二次任首相,成为依赖自由党支持的少数党政府的领袖。
※※※
这位社会党人首相希望:他的工党新政府将对埃及作出重大让步,在印度进行远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重新作出努力以促成世界的、至少是英国的裁军等等,借此来使工党政府扬名天下。他算定这些目的可以得到自由党的支持,因而可以在议会中赢得多数。我和鲍德温的分歧从此开始。自此以后,五年前他挑选我为财政大臣而产生的那种关系,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我们仍保持愉快的私人接触,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在帝国的和国内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应该强烈反对工党政府,应该维护英国的尊严,就像在迪斯累里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那样,应该毫不犹疑地进行论争,即使不能立即引起全国的响应也在所不计。就我所见,鲍德温已感到坚决维护不列颠帝国的光荣伟大的时代已经早就过去了;他并且认为,保守党的希望在于适应自由党和工党的力量,再相机行事,以巧妙的策略,把舆论的强烈情绪和大部分选民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他在这上面当然是极为成功的。他是保守党从来不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党务经理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对于这些一般性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够作出评判。
我们之间发生断然的决裂,是由印度问题而起的。首相在保守党的印度总督欧文勋爵以及其后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动之下,提出他的印度自治方案。于是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会议,刚从宽敞方便的拘留所中释放出来的甘地先生,竟成为会议的中心人物。至于在1929年和1930年大会中所发生的争论的详细情形,就没有必要在这部书里一一叙述了。当政府决定释放甘地,以便他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使者出席伦敦会议的时候,我和鲍德温的关系就破裂了。他对于事态的演变似乎颇为满意,他同首相和总督都取得一致的看法,断然把作为反对派的保守党引导到这条道路上去。我坚决认为,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因此不久我便为了这个问题辞职退出〃影子内阁〃。193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