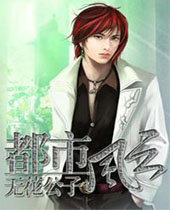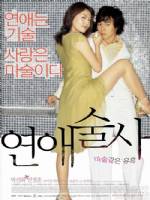景山的晚风-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者,却忧郁而死,由检不能不受到深深的震动。他凭着自己的聪颖和敏感的直觉,逐渐明白了养母的死因。原来,养母为人正直,恪守规矩,不愿与客氏、魏忠贤之流同流合污,于是招来忌恨,被百般刁难,受尽委屈。而养母又不愿申辩,即使申辩也是无门,过得很不顺心,最终积郁成疾,撒手归天。
养母的死,对信王由检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他逐渐感觉到了人世间万事的复杂和不公,并开始对周围的人和事持怀疑的态度。魏忠贤和客氏一手遮天,也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开始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学会了自我保护。
信王更多地把时间用在读书上。他自小酷爱读书,并有静坐颐养的习惯,能久坐不动,口中却念念有词。除读书之外,据说还常常溜出宫去,微服私访,接触到一些在宫中接触不到的东西。这些,对信王的成长大概也有一些影响。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天启六年(1626)年初。按照当时的算法,信王由检已是17岁了,到了婚嫁的年龄。而实际上,当时的信王仍只是一个15周岁多一点的少年。不过,这已是够上生儿育女的年龄了。对于皇室来说,多生多育,是每位成员的义务和责任,因为只有宗室繁衍,人丁兴旺,朝廷才会有坚实的根基,才会坐稳江山。了解了这些,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本朝宗室经过200多年的繁衍,至明末已有60万人之多的道理。
既然已到了婚嫁的年龄,信王由检自然就应该成婚。天启帝开始命礼部为信王选婚,寻觅适合做王妃的女子。按本朝的规矩,皇室子弟的婚配,倒不遵门当户对的古训,而是从民间选取淑女。这样做的原因,一来是因为天下虽大,但也绝对找不出能与皇室门当户对的人家,还不如从普选的淑女中挑一位。二来也是因为皇室拥有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势,很难保证本已有根有底的大户人家,在与皇室攀亲后,不利用其影响谋求私利。因此,皇室子弟婚配,一般只选那些没有什么家庭根基的平民之女。而且也只有在确定婚嫁之后,皇室才会通过朝廷,并视实际情况给予其娘家人相应的封赏,享受该享受的待遇,使得其娘家人在显赫富贵之余,也能不忘感念,饮水思源,不至于生出什么是非来。
到了五月十八日,礼部正式奏报皇上,已在顺天府共选了77位淑女备选。一月之后,天启帝令正式选婚。
按本朝的惯例,像这种宗亲的大婚之选,一般由皇后主持,外加两位贵妃陪同。淑女们被召进宫后,由皇后等人过目定夺。选取的标准,最重要的倒不是美丽动人,而是要身材匀称,举止端庄,再考虑生辰八字是否合宜之类的因素。选中的淑女,则由皇太后或身份类似的长者,用青纱布蒙盖其头,再在她手臂上套上金玉手镯之类的吉祥物,算是信物。而那些未被选上的,则将庚帖塞回那些人的袖中,赐些银两,劝慰一番遣还家乡。这样的经历,对落选的淑女而言,不仅无伤大雅,或许还会给日后的婚嫁挣些资本,因为她们毕竟是被召入宫过的淑女!
77位淑女,被一一召进宫中,由天启帝的皇后张氏及陪同的两位贵妃过目挑选。最后被选中的是大兴县生员周奎的女儿周氏。周奎原是苏州人氏,后落籍大兴。因此她的女儿或许还有些江南水乡的灵秀之气,不像一般北方女子那样粗糙。不过张皇后后来又觉得这位周氏过于弱小,大概是担心她不像能生善育之辈。当时的这位周氏,也不过是个16虚岁的少女,自然不会像成人那般丰满。最后还是那位刘昭妃一言九鼎,说道:
“现在看起来是稍微瘦弱一点,不过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得丰满健壮。”
刘昭妃是万历帝的妃子,在万历六年(1578)就与万历帝的王皇后同时册立,资格很老,而且也深受大家敬重。万历四十八年(1620)王皇后死后,这位刘昭妃便掌太后之室,住慈宁宫,说话很有分量。因此,既然她这样说了,便最后确定周氏,册封为信王妃。这位周氏后来很是争气,先后生了三个儿子,确见刘昭妃慧眼不凡。这九鼎一言,也为刘昭妃积下了人缘,后来升为皇后的周氏,待刘昭妃也很不错。
接下来便开始张罗婚事。礼部奏报信王由检婚礼仪举。闰六月,钦天监选出吉日,婚事便依此而有条不紊、恪守礼制地进行起来:
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时搬移;
十二月初八日午时当冠;
十二月十六日辰时纳征发册;
十二月二十一日卯时安床;
天启七年(1627)正月二十七日卯时开面;
二月初三日卯时迎亲,信王出府成婚;
二月初五日文武百官身穿吉服赴信王府行礼;
二月初六日信王与王妃周氏行庙见礼。
至此,婚礼便初告结束。在整个婚礼过程中,信王由检像个木偶,任人摆布,没有什么发言权,直到最后才出场。这样的婚姻很难有什么幸福可言。不过信王后来与这位周氏的关系还算过得去,这真是十分难得的。
既然已经结婚,信王便不能再住在大内的勖勤宫了,而应该兴建一座像样的信王府了。四月,皇兄天启皇帝下令兴建信王府第,遣工部尚书薛凤翔操办。
不过,当时的国库中实在没有多少余银可供大兴土木。辽东的边饷,像一个无底洞,总是填不满,弄得国库匮乏空虚。而就在前不久,信王的3位叔叔,即瑞王常浩、惠王常润、桂王常瀛,分别被遣至汉中、荆州、衡州的封地,破费了不少钱粮。或许是国库已空,因此三王之藩的仪物礼数,已是很将就马虎,能省即省。不过也有人说这是魏忠贤故意以为国节费的名义刻削贬低的,这多少有点冤枉。当时的国库实在拿不出什么钱来铺张浪费,而魏忠贤当然也不会拿自己的钱来为皇帝撑什么场面。
既然无钱,自然就应变通。于是内官监太监李永贞提出把惠王常润原先居住的惠王府修理装饰一番,改成信王府,一来惠王府空着也是空着,二来国库也实在没有余银来新修信王府。这一方案最终得到天启帝的首肯。经过修葺之后的惠王府,便改成了信王府,由信王搬入居住。
这种安排,对信王由检多少有点屈就。不过,此时的信王已能体谅朝廷及皇兄天启帝的难处了。为节国用而委屈自己,对信王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就在这年的正月,信王还辞谢了皇兄赐给他的地租银两,理由是“边境多虞,军费甚匮。”不过,信王也从这些经历中逐渐懂得,即使位尊天子,也离不开那些白花花的银子。
当信王后来成为崇祯帝后,他便开始嗜财如命,拼命为自己捞钱积财,而且一毛不拔,一如他的爷爷万历帝。他的这种做法,不知与他做信王时的这些经历有无关联?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崇祯登基(1)
信王由检绝对没有要做皇帝的准备,朝廷上下也没有人想到他竟然会做了皇帝。
在不太懂事时,信王曾不知深浅地问过他的皇兄天启帝,能否也做做天启帝做的那个“官”,皇兄当时也开玩笑地说这个“官”可以和他轮着做。不过这毕竟是戏言。据说信王也曾有过诸如梦见乌龙蟠绕殿柱、在宫中花园的两口井中同时打到两尾金光闪耀的金鱼之类的吉兆。但这些毕竟只是可信可不信的附会而已。懂事以后的信王,熟诵《皇明祖训》,对其中那些严禁诸王非分之想的训词,当然不会陌生。本朝为防止诸王乱政夺位,早已作了种种防范,真有点甚于防贼的味道。对这些,信王自然也懂。尽管皇兄天启帝一直没有子嗣,但皇兄才过20,年纪轻轻,想来也不至于绝后,而要弟弟接位。因此,信王也一直是安于现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过,命运往往就是这样造化人,由不得你自己!天启帝的突然驾崩,竟然使信王由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匆匆登上了皇帝宝座。
天启七年(1627)八月中旬,宫中突然传出天启帝病重的消息。
天启帝当时只有24虚岁,按理不应如此。据说在天启六年(一说是天启五年)八月,天启帝祭祀方泽,在回宫途中,曾去西苑荡舟游耍,不幸落入水中。冷水浸袭,加上惊吓,从此落下病根。不过,一般人是不会知道这些事的,因为万岁爷的身体状况,尤其是生病之类的机密,只能是少数的圈内人知道。试想,被臣民口口声声颂作万寿无疆的万岁爷,突然得病,岂不尴尬?又有谁能保证天下臣民能不由此恐慌而致天下不安?甚至一小撮居心叵测的大逆不道之人乘机捣乱?因此生病之类的话是说不得的、传不得的。越是有病,越要把万寿无疆喊得更响。一来算是祝福,二来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做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情。
不过,臣民们还是能从一些迹象中猜测到一二。魏忠贤的从子魏良卿不久前曾代天启帝享南郊、祭太庙这一反常举动,多少证实了这种猜测。果然,到了八月十八日,天启帝的病情恶化,看来是不行了。于是魏忠贤便与群臣商议,能否用“垂帘居摄”的办法应对。阁臣施凤来认为此举不妥,便说:
“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得!”
意思很明白,就是此举行不通,而且群臣也一致要求信王入宫视疾。
据说魏忠贤也为此找过天启帝的皇后张氏商量对策。按魏忠贤的设想,是令宫妃中的某一位假称有孕,而将魏良卿之子领入宫中,接替皇位,由魏忠贤摄政,就像“新莽之于孺子婴”那样。此计关键是要有皇后张氏的通力合作。然而皇后张氏与客氏、魏忠贤宿有怨恨,而且张氏为人正直,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会含糊。因此当魏忠贤派来的人刚刚把话含蓄婉转地说完,张氏便严正拒绝,而且把话说得没有任何余地。她说:
“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话说到这种分上,魏忠贤也就不能再做下去了。
八月二十二日,信王由检被召入宫。
在此以前,信王只能呆在信王府中,心里虽然着急,但面上之事则不敢轻举妄动。按理,皇兄病重,信王作为至亲,自然应早早入宫,尝药视膳,嘘寒问暖,方显兄弟亲情!但事实上,信王绝对不敢造次,除非有皇兄明确的旨意。因为这时的信王,已深知政事的复杂、人心的险恶。如信王入视,当然可以被说成是出于兄弟亲情,但如果有人反过来讲,说信王在皇兄尚未驾崩之时,就上窜下跳,也未尝不可。这种做法,轻则可以说成是信王沉不住气,急于接班,重则可以说成是信王早有异心,妄窥大位,只不过是此时才显出本色。不过,此时已有皇兄天启帝明确要他进宫的御旨,情形就不一样了。
信王由检进宫见到皇兄后,自然是亲情尽露,同时也有点诚惶诚恐。此时的天启帝回光返照。他侧身靠在床上,看着弟弟信王,眼光中包含着无限的哀怜、惜别之情。他对弟弟说:
“到我跟前来,你当为尧舜之君!”
此言一出,信王直吓得瞠目结舌,根本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信王才结结巴巴地说:
“臣死罪,死罪!陛下说这样的话,臣应万死!”
信王深知皇兄话中的含义,但又不敢确定真假,谁敢保证这些话不是皇兄乘病之机对信王的考验呢?不过,此时的天启帝自知将不久于世,倒是诚心诚意地说这番话的。他对信王再三劝慰,并明确告诉信王说:
“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
信王听毕,更是万般恐惧。他转而与身边的魏忠贤搭话,诚恳地称赞魏忠贤,说他侍候皇兄,劳苦功高。魏忠贤当然是语气温和地谦虚一番。随后,信王立即出宫,像逃窜一般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就在信王入宫之前,天启帝还撑着病体,召见阁臣和五军府、六部、都察院等部院大臣,以及科道官员,已把身后由信王接位的意思告谕诸臣,并说:
“魏忠贤、王体乾皆恪守忠贞,可计大事。”
此言大有他们办事、朕即放心之意!魏忠贤的死党、内阁首辅黄立极立即回答:
“陛下任贤勿贰,诸臣无不仰体!”
话说得很明白,意思就是陛下您放心去吧,群臣会照办的。
至此,天启帝大概已放心了。就在召见信王后没多久,即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申时,天启帝在懋德殿驾崩了。
据说,魏忠贤至此仍未死心。他没有立即公布天启帝的死讯。但朝臣们已纷纷听到消息,在第二天天亮时都不约而同地赶到宫门,要求入宫行哭临之礼。守卫宫门的宦官却不准他们入内,说是要换丧服;百官回家换成丧服赶来,宦官却又说先帝尚未成服,百官仍不能进宫哭灵。如此来回折腾了三四回,气喘吁吁的百官在百般哀求之后,才得以进宫,行哭临之礼。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崇祯登基(2)
百官们进宫之后,只见魏忠贤、王体乾等少数几人守护着归天的天启帝。魏忠贤两眼红肿,侍立灵侧,不发一言。而王体乾则来回往复,忙着安排礼部官员准备治丧礼仪及器物用品。群臣礼毕退出后,突见内使十余人急出,传呼崔尚书(兵部尚书崔呈秀)。崔呈秀一人复进宫内,与魏忠贤密谈,具体内容无人知晓。有人推测,可能是魏忠贤与他重谈篡位自立之事。因为在此以前,魏忠贤曾召崔呈秀、田尔耕密谈过篡位之事,当时田尔耕诺诺连声,崔呈秀则是不肯表态,魏忠贤再三追问,崔呈秀才说:“恐外有义兵。”魏忠贤于是作罢。此次密谈,是否仍是旧话重提,而崔呈秀是否仍是力阻此举,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后来有关此时的材料,都是不利于魏忠贤的。魏忠贤既是十恶不赦之徒,给他多加几条罪状也无碍大事。人们更愿意相信,像魏忠贤这样的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