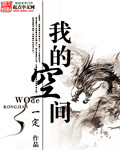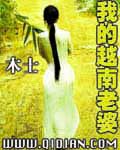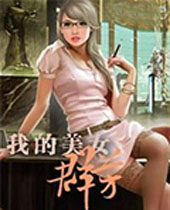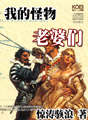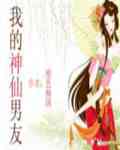我的非正常生活-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确是性情中人的上司共事。
mpanel(1);
偶尔,在某一天大家的心情和天气都阳光灿烂的时候,晃也会问我:你说我是
不是不应该在办公室里骂人?是不是太伤人家的自尊心了……我真的不置可否,我
想像不出一个不再骂人的不再随性的温吞的洪晃是个什么怪模样?!
和洪晃虽然认识六年,共事两年,写到这里时我对这篇文章心里依旧非常没底。
晃是一个故事太多的人,以至于当我提起笔时,脑子里闪现出许多缤纷的画面,哪
一个画面又都无法定格。我不知道当年晃的父母为她取名叫“晃”,是不是预料到
了她后来“晃”的天性———一个可能一生都会特别活跃的人。
第七章
小雪眼中的洪晃(二)新房子,旧房子
如果不算洪晃妈妈家那个北京著名的四合院,在我认识晃的这几年中,她也已
经先后置办了四个家了。大概做一本家居杂志始终是晃心中的心愿,我们都觉得她
简直是热爱装修、热爱设计、热爱关于家居的一切饰品。
最早的一个家是在琉璃厂里的一个小小的平房院,大概房子加上院子也就100
平方米。所以晃的设计天才得到了充分发挥,床在大衣柜的上面,就是说上床要趴
梯,床板上面伸腿就能够到房梁,床板下面是大衣柜,卧室和洗手间是一体的;厨
房和客厅是一体的,屋子里的东西很多,可是觉得空间还挺大。
大概这个家的确太小了,晃随着一群艺术家“到农村去住”的搬迁热潮,脑子
一热在昌平一个山沟里买了一块地,这回大发了,她要在这片空地上自己盖一座房
子!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吓坏了,这块地里杂草丛生,凹凸不平,而晃和男友两个人
蹲在地上在一大张废报纸上画着各种我看不懂的横线竖线。当时我觉得,这俩人也
就是玩玩土木游戏,这房子盖不起来。
但是几个月后,房子真的盖好了,我还荣幸地被邀请成为第一拨入住的嘉宾。
房子是一长溜的形状,外面的颜色红黄相接,我老觉得有点像聊斋里的房子。里面
基本上是中式的风格,有一些漂亮的木棱窗和门。这房子被《家居》之类的杂志拍
了数十页作为乡间住房的经典作品登出来。
这个昌平的小院得了主人两年的宠,主人已经又有新想法了。大概晃实在不堪
忍受每天来回三个小时的上班车程,如果碰到雨雪的坏天气就要花半天时间在路上。
晃终于决定还是在城里租个公寓,平时可以安身。她很快在三里屯附近租了个100
多平方米的公寓,因为房子是人家的,装修也是现成的,所以两人的设计情结没机
会发挥,很是郁闷。
这间公寓显然不太合晃的胃口,所以不到半年她就找到了新的目标。这就是一
间废弃的400 多平方米的工厂厂房,晃和男友一时兴奋得像当年在昌平买了那块地
一样,很是激动了一阵子,动不动就邀请亲朋好友去她们家的“厂房”参观。同时
浩大的装修工程再次启动。
很块,又一个新家诞生了,200 多平方米的客厅大得有点让人晕,迄今已经成
了派对的专用场地,并且还成功组织了一场电影的新片发布会。不做作的爱情
在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中,对于一个“好女人”的爱情观的定义很简单:你要从
一而终无怨无悔地去爱一个男人,最好让一生如一日;要是你恰好不那么幸运地结
过不止一次婚,你也最好将自己收拾得在外人面前像一个纯洁的不谙世事的女孩。
我不知道晃的爱情教育是怎样的,在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就从不忌讳她的离
婚,她的旧恋情和新恋情。
我听到过不止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男性朋友都说,洪晃是他们一生中认识的女
人里最聪明的一个。事实上在我们交往和共同工作的几年中,我已经深深领略了晃
作为一个女人的出色。
我私下里曾经很困惑,这样一个聪明的女人,究竟什么样的男人能配得上她呢?
后来发现,对男人来说,晃在生活中是个很容易“打发”的女人。因为她经济上的
足够独立,她的男朋友不必为女朋友今天要月亮明天要太阳而头痛;因为她的独立,
她可以明明白白地为自己在事业上做决定,而不必劳神男朋友;因为她个性的率真,
她的男友因此省心很多,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恋爱中的洪晃和大部分女孩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概脾气烈的人看上的都是
表面温和,实际上脾气也是一点火就着的人,所以也会看到两个人很认真地吵架,
在两个城市用长途电话“吵”上几个小时。我赶上过一次,晃一直在用电话和男友
“理论”,手机电池用光了,接着用座机,从我们出去吃午饭到我们回到酒店,晃
一直保持一个姿势,表情丰富地对着电话大呼小叫,当然,依晃的语速和反应,男
友也基本上只有听的份儿。
mpanel(1);
这样的小故事都是两三年前的事了,这一阵子倒是听不到他们两人的吵闹声,
除非是在装修的问题上,两人都自诩为“大设计师”,都视室内设计为自己的最爱,
并且都很难说服对方。
晃是一个很享受自己爱情的女人,在这一点上,她是一个不用“猜测”的女人,
脸上的幸福和心中的幸福永远步调一致。而这一点,其实是挺难做到的,需要一个
女人有不做作的本性,还需要她有真的爱情。
第八章
童年时我身边都是
摩登上海女郎
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据说出身不是特别体面,是吃青春饭的。据我妈说,
我外婆年轻时候的风格是她永远在旗袍的扣眼里放一球新鲜的茉莉花,每天都换。
解放后,我外公从香港回到北京,外婆就带着我妈从上海搬到北京。
开始,他们住在东四八条的朋友家,等我出生的时候就搬到史家胡同现在的四
合院了。我不记得外婆穿旗袍,可能是那时候她老了,也不记得她有茉莉花,但是
记得她是全胡同最特别的一个老太太。她留非常短的头发,每一根都整齐地背到脑
后面,没有一丝乱发;她穿的衣服永远是素的,没有花的,颜色永远是各种调子的
黑、灰和咖啡;她对料子非常讲究,夏天当然是各种丝绸裤子和中式衬衫,冬天是
呢子的裤子和中式外套,有时候外面还穿一件缎子的棉背心。
我至今还有一套我外婆梳妆用的银具,每一件都是精雕细刻。我从小有个感觉,
外婆是个很讲究的人,她喝茶永远用一个小的紫砂茶壶,白开水永远是放在一个小
铜壶里面,夏天我渴了,拿起壶来对嘴喝水总是要被外婆训一顿,她永远把我的错
误归结为保姆和北方人。
除了外婆、干妈,还有黎姑姑和夏姑妈。黎姑姑叫黎明辉,是上海30年代的影
星,据说她由于唱了一曲叫《毛毛雨》的歌而走红。解放后就当了幼儿园阿姨。我
4 岁的时候,父母再不能忍受我在这些30年代摩登女郎身边鬼混,死活要把我送幼
儿园。外婆先是不同意,后来妥协了,条件是我只能在黎姑姑当阿姨的幼儿园待半
天,这样不会染上太多的北方人的坏毛病。
夏姑妈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女人,天天小酒喝得高高的。她是从巴黎回来的,
所以也非常讲究穿,在我的记忆中她比外婆要洋气,头发烫成大波浪,也是一丝不
苟地捋到耳朵后面。
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我的干妈做的。如果当时有时尚刊物我干妈可以当服装编
辑。她天天研究什么百褶裙、背带裙、连衣裙、卡腰、下摆、袖子的收口等问题。
每个周末她的到来都是十足的一场时装秀,她每次都穿得不一样,衣服都是她自己
做的。干妈就像我的形象设计师,每周都带新衣服来,都不一样,都是她的设计,
也是她自己缝的。衣服带来我就得换上,然后还要摆姿势、拍照。有时候外婆高兴
了就请所有人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冬菜包子,或者去新侨吃西餐。
从某种意义上我是这些摩登女郎的时尚发泄点,60年代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打
扮自己了,而她们一生惟一的嗜好可能就是打扮自己。解放后,她们已经不能在大
街小巷随心所欲地炫耀自己的时髦,我这个关在大四合院里的女孩,正好是她们的
时尚发泄和挥发的一件小玩具。
我妈妈是个大美人,这是我在她调到外交部,从湖北干校回来那一天发现的。
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在她从月台到车站的隧道中走出来那一刻,我有一种由衷的
自豪,我发现我母亲身边似乎有一个光环,她比别人都亮。至今她的光环犹在,当
她走进一个房间,她就是中心。我妈妈的美比上海那些摩登女郎要含蓄得多,我当
然更喜欢我妈妈这种风格。我妈妈那时候都是穿很严肃的制服,但是我记得她总是
有一件非常好看,颜色鲜艳一点的衬衫或毛衣穿在深色制服的里面,露出一点点鲜
艳的领子。到了70年代,妈妈已经是外交部长夫人的时候,她的美容用品也不过只
有檀香肥皂、友谊牌擦脸油和美加净牙膏。妈妈出国带回来吃的、小人书,从来不
记得她买什么口红之类的东西。
1970年我外婆去世了。这是我童年的一个句号。同一年,我妈妈走后门把我塞
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念英文,当然是为了我的前程考虑才这么做,可
是我那时候9 岁,不太理解这一切,只是觉得我的好日子没了。
刚进这所学校时,我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太用过。在史家胡同小学的时候,我外
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尿——脏,憋着回家再撒。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我根本不
会用蹲坑厕所,只会用抽水马桶。同学们笑死了,没见过9 岁还不会撒尿的小孩。
我小时候几个摩登女郎精心培养的服饰美容意识大概在半年内就被彻底革命化
了。在我学会用蹲坑后的不久,就开始改变我所有的服装。要穿军装,要白衬衫蓝
裤子,要穿解放鞋和军鞋。1973年,我妈妈再一次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纽约。
就这样,在短短12年里,我的“时尚观念”从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无产阶
级专政又到了70年代纽约嬉皮。从此以后我彻底乱了,也就不想了。
第九章
纽约空降红小兵(一)
我12岁那年,北京外语附校的期中考试提前了,考得好的学生被拉到离学校挺
远的医院去体检。大概过了两个月,学校才宣布有十几个被外交部选中做小留学生,
将被派到国外去学外语。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是不是特别兴奋,但是我想即使是高
兴得要跳楼,在当时情况下也要压着点情绪。这跟旧社会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
欢这男人越要哭得伤心,真流露出愿意嫁出去,说不定这门“亲事”就黄了。
人定下来之后,外交部好像给我们开过一个学习班,讲了什么我真一点儿也想
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
这使我们28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任务非常艰巨,
但绝对光荣。
临走之前,外交部发给每人700 元人民币服装费,在1973年,这简直是一笔财
富。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28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
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我们协商要穿一样的衣服,
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
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心里一定非常温暖。
就这样,我和三个去美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路过巴黎去纽约。法航
的空姐微笑地欢迎我们,我们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
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们住在大使馆,到了纽约我们被接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出
门,讲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
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
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
知道这叫T 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
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
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最可怕的是所谓的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把破吉他、破口
琴,没音没调,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
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的同班同学。
在学校里的头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4 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
天早上“林肯”把我们送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开始打呼噜,小红房子学
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爬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
吃糖,所以睡觉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交2000多美元的学费,
真是学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乌纱帽要搬家。那时候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
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她想出个鬼点子,让4 个孩子全住到美国
人家里去。我是第一个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
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画。家中有3 个孩子,吕贝卡、
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5 岁。大女儿吕贝卡
是我的同班同学。选家庭时,代表团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