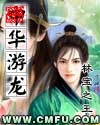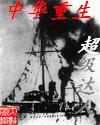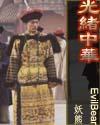中华野史-第108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不为风气所转移。誉之者则曰讲尔新旧,立宪元勋;毁之者则曰骑墙中立,无性执拗。然窃尝平心论之,毁者庸或过情,即誉之者亦未尽得其真。天生文襄,为德宗也,先德宗而兴,后德宗而死。凡德宗三十四年之事实,磊落轩天地,危疑亘古今,而文襄张公,实惟有以辅之翼之,疏之附之,患难与共,而左右朝局也。继湘淮诸勋臣之后,声施烂然,超出于李高阳、孙济宁、阎朝邑、王仁和之上,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
方德宗嗣位之年,正文襄张公声誉踔起之日,抵击权贵,声震一时,有清流六君子之目,而文襄实冠其曹。尤难者,吴可读以一死位请懿旨,预定他大统之归,廷臣奉旨,阐明圣意,内阁集议,各执一说以上闻,类皆模糊影响之谈,文襄独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懿旨,以吴可读谓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当虑者而尚或未及深虑。海内士夫读之,始景然于经术之可以黼黻文治也,几疑高邮王文肃、金匮秦交恭诸大儒复生今日,而翕然以湛深经术目之,谓足以继曾文正遵议大礼一疏之后。自是以来,京朝风气丕然一变。士大夫始知朴实之可宝,一扫咸同以来拘虚空疏之习。此文襄之学问,有以牢笼于一世,而卓然开风气之先者也。若沾沾以平反东乡冤狱归美文襄,此其浅焉者矣。
洎以领节钺,镇封疆,三晋为其发迹之地。承丁戊大祲之后,锐意以辑流亡,振吏治为事,截抵摊捐也,办理清查也,抵补铁价也,禁止水礼也。他若大修太行官道,奏减五路差徭,凡足以苏民生之疾困者,无不惟日孜孜,与民更始。见之者以为林文忠之抚吴,潘敏惠之抚皖,不是过也。而其烛照利弊,能先天下而痛除毒害者,则犹在于严禁境内栽种罂粟。使朝廷诚于此时,著为令甲,颁行天下,其流毒何至如此之烈!尤足以动人之悲思者。俄而擢任两厂,迁移两湖,即又毅然以开通风气为天下先。请两广铁禁,试造浅水兵轮,筹设华侨领事,创办水陆师各学堂,奏开汉阳铁厂,创办机器纱织局,兴办京汉、川汉铁路,赎回粤汉铁路,争议澳门界约,凡其所设施、所规画,无非于端倪未著之秋,洞烛机先,造端宏大之,力辟当世之震撼危疑,而坚定不摇,卒底于成。当其事机盘错,万口噤声,人方虑文襄无下手处,而文襄独纡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贴妥,又如东风吹枯,顷刻变色。由是海内之谈时务者,翕然归之。有识者至比之干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傅文忠之经略金川,谓其公忠体国,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不规规于近功,有过之靡不及矣。所微不慊于人意者,规模过大,更事过多,而用度或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在粤时至开赌禁以充军饷,在鄂二十年,所贷洋款以千万计,悉以供行政上所糜之费,而抵抗舆论,力主压抑,时于晚年之行政上,微露其机。论者往往以是为文襄惜,然要而言之,三代以下,卒少完人,有大醇者不能无小疵,理或然耳。
第十一节 张文襄征调入京
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今日之死,国民之觖望,政府之失援,庸讵初料所及耶?监国为大势所迫,将起用袁世凯,使张之洞而在,亦必力主此议。当一九零七年七月,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首调张大臣入京,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征调人京。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然两大臣行事,虽偶有微异,而其宗旨则如出一辙也。近者新主即位,张大臣迭经选调,舍总理路政各务外,稍见失意。至其对于粤汉债款一事,以张大臣一生正直之人,而忽前后矛盾若是,似可毋庸深底。顾就张大臣督办铁路以来,观其所行各事,张大臣固极知中国路政亟应发达,第因国人不肯出资助之,遂不能竟其硕画耳。
张大臣之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然于极易达此主义之时,而竟不出此,则此言亦殊难信。试观中日之战,上海之中立,能安然无动者,固伊谁之功也?汉口海关十年总报告册曾谓一千九百年,北方拳匪之祸,至今印人人心。寓海外人,时为惴惴然,皆颂感谢鄂督张之洞出其毅力禁遏排外之举,以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云云。然则张之洞亦何尝排外哉?张公之洞一生最盛之勋望,系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零三年出督湖广之际。此数年中所成之巨业,如汉阳铁厂为京汉铁路制造铁轨,湖北纱织局之挽回利权,以及振兴该省各项商务,皆无可以訾议之处。而设立造币局一举,尤未可轻忽视之。惟论理财问题,则张大臣未见出色,彼仅知纸币可以济财政之窘迫,而不顾道理之合否。观其与德国公司所结之合同,足见张大臣于钱价之贱,为中国最易中毒一层,固识力之未逮也。
张公之洞之政才,已纵论如前。尚有一最大之美德,今日政界之各员所不能望其项背者,则廉洁是也。彼曾历居要任,不患不能积财,然乃一介不取,恐身后仍不免济贫而已。闻彼在武昌时,曾因需款孔亟,出其珍品付诸质库。且张大臣学问,颇占声誉,著作甚富,今日选为今上将来之师傅。要之张之洞实为一机敏难测之人物,为中国旧世界之政才。其思想随时变动,今当朝政紊乱之时,正可展其长才,而忽出世以去。吾人对此,惟有一言可以抒钦佩之忱曰“公何不迟生五十年耶?”
第十二节 张文襄之政绩
戊戌之初,朝廷改革已见萌蘖。其时康有为复设保国会于京师,未几即被御史劾散。今学部侍郎严修方,为贵州学政,奏请开经济特科,以求得人应变,朝议从之。公遂保举知名之士三十余人,康之弟子梁启超与焉。其后康复疏言国危,工部堂官不为达。给事中高燮曾乃上章荐之。故相翁同龢,复面保康才可大用。徐致靖复力保之。斯时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而先期降旨召公人都,以公为孝钦皇后手擢之人,且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故也。公闻召行抵上海,翁同龢诸公谓不可恃。值湖北有小教案出,遂有廷命,命公还任。
公既窥见朝端水火,新旧之隙侵深,遂变节而有阿附容身之举。
盖以是年四月二十三日,方有变法之诏,而二十七日即有朱逾,令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日复降旨,令在廷臣工及文武大员补缺受赏,必诣皇太后前谢恩,或具折,又以荣禄为北洋总督,皆四月二十七日事之捖兵权。公盖逆知变法无成,而大祸将作,故遂不得不急求自保矣。及政变后旧党之焰,如鼎镬之逼人,李端棻、徐致靖父子、陈宝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数十人,或杀或逐,天昏地暗。或谓公因自保,故实与其事。盖当时湖南有新公羊学说出,大肆衍播,以为改制度,而公则为《劝学篇》以遏之。又有湘人王廉之徒,立论排牴公羊,仇新政,议者谓出公意旨。由是党人益仇公,几欲将其向日声名,堕之于涂炭,舆论亦稍稍抨击,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矣。
相推相激,遂有己亥立嗣之变。方是时,惟刘忠诚上章切谏,公则援吴可读以自解,不敢稍立异同。庚子北方大乱,拳祸滔天,浸至五忠被杀,袁、许皆公门弟子,有声于政界者。
闻公此时,惟日啜泣,曾遗恺军北上勤王,然道梗不达。先是李文忠由粤督应召人都,逡巡于沪上,力持保东南策,刘忠诚亟赞成。公鉴于大势,亦力主其议,遂由江鄂共派陶森甲到沪,与各国领事结东南互保之约,所全实多。顾当时有党人据于沪汉,不乘虚蹈瑕,戮力于北,而转欲于东南完全之地,举兵起事以勤王召号,计疏事泄,遂有唐才常、傅良弼等流血于武昌之案。微闻案发,公对幕友叹息云“今日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其意欲出唐等于死罪,鄂抚于荫霖执不可,公亦不敢固争。辛丑和约后,公府物力,亦萧然扫地。然朝议方欲再练新军,以镇畿辅,遂复遣大臣南下搜括,与己亥刚毅南下之情事略等。顾此两次,公皆力拒之,以此湖广财政,终不似苏浙之缺,则公之力也。湖北担任辛丑赔款,其始分取各州县,其后公于土膏捐中求得之。乃令挹原款以兴地方学务,故湖北地方小学,不忧费绌,亦公之力也。
第十三节 张文襄之学问
使南皮而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之间,占一席之位置。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常熟而后,主都门风雅之坛坫,可无疑也。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吾于南皮其殆同此感情矣。
南皮生长世胄,少时即有神童之誉,壬子领解时,年甫十五龄耳。其后踬礼部试者十年,而后捷南宫,擢高第。庚申会试,嘉定徐侍郎致祥即套袭南皮领解之文,竟魁多士,而南皮反落孙山,艺林至今传为佳话。其癸亥殿试对策,独能屏去一切格式忌讳,畅论时事,洋洋数千言,识者以拟苏长公、陈同甫,阅卷官初拟大魁,及进卷拆封,两宫忽抑置第三。盖是时翁文端公心存方领弘德殿事,授穆宗读书,而其子同书,以败军下狱拟辟,两宫欲安文端之心,故擢其孙为状元以慰之也。
实则翁曾源之文学,出南皮下远甚。南皮学术,好立异于人,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其先倭文端、唐确慎诸公,方主辇下牛耳,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而朴学渐即衰替,北方士大夫,更不知汉儒家法为何事。南皮生于世族,富有藏书,独博览经史,以马、郑、贾、孔之学为天下倡,文衡所至,必拔取渐闻殚见之士,一时士习为之丕变。所著《书目答问》、《輶轩语》两种,至于家有其书,辇下书值为之奇涨。厂肆书贾,悉颂南皮德不置,亦可见其势力之伟大矣。其督粤时,甄录国朝儒者考证史学诸书汇刻为《广雅丛书》,欲以配阮文达之《学海堂经解》,为乙部巨观,而取富卷帙,别裁未当,榛楛勿剪,琐碎已甚,读者竟弗之重也。
南皮之以新学名世也,在既持节开府以后。平心论之,非真有见于变法之不可缓,特以举世之所不为,欲独辟非常之境界耳。故其于西学也,即以汉学家章句训诂之法治之,博而不精,知其所当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其由新而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盖康氏之进用,由于南皮之荐剡,迨其后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以彼料事之明,逆知后来必有大祸,因授意门下士某君作为此书。
第十四节 张文襄之奇才
方毅皇大婚,乐章房中三奏,及《钦定平粤平捻方略》书成,两次表文,悉出公手笔,上览之称为奇才,下诏加衔,是为公结主向用之始。光绪庚辰进官侍讲。斯时使俄大臣崇厚,赴俄议收伊犁,顾为俄人厚结所绐,竟割极边要害与敌。公即上疏力争,凡十余上,陈论战守方略甚悉。是时,左义襄公方乘战胜之威,驻兵乌鲁木齐。公欲乘间张国威,力主战,且云“战即不胜,犹可以天山南路界英,连兵复战。”其言虽堕书生策士之见,然俄卒震慑,曾惠敏公得以折冲坛坫,而尽毁崇约,争回帖克斯川之险要,并拓阿尔泰承化寺北界线。朝廷复治崇厚罪,公之向用乃益殷,两宫皇太后乃敕译署,令遇事与张之洞商矣。辛巳进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逾年遂擢山西巡抚矣。先是,丁卯公承命为浙江考官,得士尤众,拔茅连茹,称盛于世。其后成名者,如陶制军模、沈布政镕经,许侍郎景澄、袁忠节昶、孙刑部诒让、王山长棻、谭大令廷谳,均著伟业盛名于世。余如沈吾士善登,则邃于算术,钱孝廉丙奎,则深于律吕两君尤近代绝学,皆公所罗得者。及官湖北学政,则立经心书院课士,成就尤众,刻有《江汉炳灵集》。迨癸酉典蜀试,旋为学政,复建尊经书院,刻《輶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士,所得高才生,如杨锐、廖平、宋育仁、王光棣、王秉恩、吴德潇等,皆尊经书院受学者也。又如名宿之士,为公收置门下者,如蒯观察光典、缪京卿荃孙、樊方伯增祥、王
侍郎文锦、王祭酒懿荣、郑贡生知同、易观察顺鼎、左口部绍
佐、袁刑部宝璜、林太史国赓;咸使之相与切磋,以通经致用期许。曾文正尝嗟异之,以为洪北江、朱笥河、阮文达督学,所以搜岩采干者,不过如此云。盖公于是时固以朱阮自许也。
公之抚晋也,首以禁种罂粟为务,而于差徭尤急意清理,且修井陉大道,以便商贾,晋民承灾沴之余,以苏其困。时阎文介长户部,以公所为有古大臣疏通知远之风,故遇事多乐赞之。会法越事起,应诏密陈战守机宜十七事,又密举中外文武人员五十九人。甲申春,内召密奏越事,遂命署两广总督。时值桂抚徐延旭、潘鼎新,溃军于镇南关外,越之北宁、山西、高平、谅山连陷,法水师提督孤拔,方率师船,纵横于闽广海上。台湾尤岌岌,仅赖淮军宿将章总兵、高元,肉薄夺取基隆炮垒,歼敌无算,祸用少。时公与彭刚直公,规画粤中战守,修虎门、横档大角沙炮台,形势稍固。彭刚直以公机敏达事,每推重之。公遂疏荐桂臬李秉衡办理粮台,旋擢署桂抚。又密保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北海镇总兵王孝祺,募钦、廉、材、武敢死之士,将以出关,遂有谅山之大捷,为近世中国战史上第一奇功。法提督亡于阵,法之议院大哄,遂起攻其政府,首相茹连斐里告退。公与彭刚直以敌可乘也,请因势进兵,规取北宁河内。会马江师覆,朝议方羁于缔和,不许公奏。公与彭公抗疏力争,言至痛切,海内读者皆感动。然庙谋已定,弃越不可挽回,惜哉!而公因是与李文忠有隙矣。公为疆吏,颇师胡文忠之救邻,无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