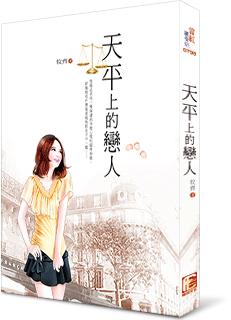地板上的母亲-第6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开花的泡桐,就要开花的洋槐……闹吵吵的小鸟儿,隐伏田间的野兔,无数忙碌的昆虫……贪心的我还想见桃花盛开在油菜花海上的样子,想见枫树、柿树和乌桕树变红变紫,把影子投在水中的样子,想见玉米腰挎红缨、葡萄挂起串串玛瑙珠子、西瓜甜瓜撂一地的样子……天和地酿成这一派生机,浓浓的,嫩嫩的,光光滑滑的,不是奶汁是什么?一颗倦怠的心被它喂饱,所有皱褶都鼓胀起来了!
要是有一叶竹排多好,顺流而下,一直漂到烟波浩渺的白龟山水库,畅快的心意会串起多少有滋有味的浆果,让灵魂美美饕餮一番啊!
大浪河,让我从一个人的背影里转过身来,重新拥有了整个世界。
第六章 妈妈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
妈妈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1)
亲爱的小星星:
昨天说到收割过的地亩,你说你看到那些被挖得窟窟窿窿的田土,心中就恼那些挖观赏草的人。看着你滴溜乱转的眼珠,我就知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你对它们并不关心,你关心的是去那边的水上划船、玩打仗,你的心已经被都市的游戏圈禁了。你看不见地平线,也看不见植物们庞大的地下根系。不过,你可千万不要认为乡下的孩子没有玩具,妈妈小时候玩过的东西可比你多了去了,并且我们玩的环境也好到了天上。
在地里剜菜的时候,我们玩扎鳖。选一棵最大的野菜挽个圆圈儿,埋进一堆虚土里,让对手拿根坚硬的草棍儿扎。当然,埋的时候扎的人不许看。如果扎在圆圈儿里,这棵菜就归扎的人,如果没扎住,他就得赔一棵,然后轮他埋。太阳晒得身上的小布衫发热,人坐在风吹麦苗扑啦啦响的旷天阔野里,任凭干净得不沾手的土坷垃在裤管和衣服的皱褶里灌满又滚落,直玩得身上汗津津,眼睛发光,头上长草,那感觉就像在老天爷的大斗篷里荡秋千。
麦黄梢,树上的楝子儿蚕豆大,我们会爬上高大的楝树,摘几蓬青青的楝子,在雨湿未干的地上挖几个坑玩丢子儿,和你们现在玩的拍画片差不多。几个人撅着屁股趴地上玩得兴兴头头,连吃饭都忘了。天热了,结伴儿去河里捡石子,不但比谁捡的石子好看,还要比谁的能打出火。一只手拿一块小石头,“叭叭”对着砸,砸得
火星四溅,然后把烫手的石头放到鼻子下面闻,一股窜鼻子的火腥味儿直往肺腑里钻。
夏天歇晌儿,就找个树凉阴大的地场儿,或是屋高墙厚的房山头儿,围在一起抓子儿。七个子儿是拿碎瓦片儿砸出来的,细致的女孩儿砸好后还要找块涩涩的新砖磨得浑圆溜光,玩出垒垒叠叠的花样儿来。没有好子儿的时候,就捡几块结实的坷垃蛋儿或是石头子儿代替。跳绳最好在月亮明光光的晚上,没有电灯晃眼,随便在谁家院前屋后找个光地儿,分班儿跳长绳,或是单个比赛跳花绳。直跳到夜深人静露水下来,打湿了放在地上的衣衫。冬天冷,白天踢毽子,晚上捉迷藏。半轮月亮在天上,撒下来的不是月光是冰冷冰冷的霜粒。大人们跺着脚喊:“小兔崽子们哪,鼻子都冻掉了还玩啥哩玩……”几个孩子趴在黑影里连大气都不敢出,大人们不知道,满世界驴里马里跑,我们头上正冒汗呢。
河那边的县城野兽一样静静地卧在蓝琉璃罩似的天空下,半腰里长着两棵小树的砖塔直刺青天深处。再远处是比天蓝得更深些的桐柏山,
神话一样横向半空。目光所及,四季飘摇的是庄稼的海洋,看见一条路我就会想,从这儿出发能走到那儿去呢?
亲爱的小星星,你可别笑生在穷乡僻壤,没见过大世面,也正因为这样,我的童年才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拥有了对这个世界清澈无边的向往。
茶罐
“咱河南——
千里依——
麦也麦浪黄啊……”
一个背着桑杈的大人一边走,一边唱。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远远地跟在他身后,他怎么也听不明白,千里不就是千里吗?依啥里依,那个随着东南风绸子一样抖个没完的“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无意间,这孩子抬起那只闲着的手打个眼罩四下里看,看着看着,心里有些明白了:那个拖得长长的“依”字儿啊,可能就是说这高高低低的土地,这些岗坡啊,平原啊,起起伏伏到处都是麦地。这些麦地一会儿拱起来,一会儿趴下去,风一来,刮起一波一波的麦浪,谁家的床单儿也没有这么大,大得只能这么着“依”它几百个拐弯子。
那孩子马蜂细腰瘦胳膊细腿的,活脱是一棵刚窝过脖儿的黄豆芽子。头上戴顶大草帽儿,手里提着一个瓦罐,瓦罐里满满地装着一罐茶,不是竹叶茶,就是柳叶茶,再不就是蒲公英茶。也有头一年薅回来的茶蒴,蒸蒸晒晒包在莲叶里,挂在房檐下,吸了一冬一春的雨雪味儿,这时候被老奶奶拿下来,酽酽地熬上一锅,放凉了装一罐子,让小孙子送去给地里割麦的人喝。
满满一罐茶水,就这么跟随着那小孩子的脚步往前移动,跟随着那个背桑杈的庄稼汉往前移动,被野风吹着,太阳晒着,被那人即兴唱出的小调牵引着,泅过一眼望不到边的麦浪,一步一步往前移动。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广口双鼻儿灰瓦罐,用麻绳系着。这种瓦罐也没什么稀罕的,没上釉子,通身一色,泥巴捏捏,放火上随便一烧就是了,几毛钱一个。这会儿瓦罐里装满了水,装满水的瓦罐可就主贵了,对于焦渴难耐的割麦人,它就是上天假人之手创造出来的最可口的浆果。凉津津,甜丝丝,抱起来咕嘟咕嘟狂饮一阵,那真是世上再惬意不过的事了。喝足喝够了,用手拍拍凸起的肚皮,“哐当哐当”响,逗得送茶的孩子脆声大笑。
瓦罐空了,又开始跟着孩子往回走,老奶奶正站在家门口张望呢,等大人们割一来回拐过头来,那个柳条圈儿护着不漫不溅的茶罐又该回来了。
活笸箩儿
“三翻六坐九爬叉,十个月就会叫大大。”
会坐会爬会叫大大的娃娃们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晒活笸箩儿”。因为活笸箩儿里盛满了属于妈妈的各种宝贝。
活笸箩比盛粮食的簸箩小,簸箕柳编的,密密实实不透气儿,桐油一刷,上一层清漆或黑漆,起明发亮,盛水都不漏。也有讲究的姑娘媳妇儿,把活笸箩漆成彩色或素色描花儿的,每逢做细活,活笸箩里盛着绿绸子红缎子,端出来带起一阵风,鲜净得耀眼。
活笸箩里最多的是铺衬卷儿。裁衣服裁下来的边角料儿,卷在那里以备衣服破时补。从破衣衫旧被里儿上裁下来的旧铺衬,撕成小方片儿垫鞋底儿。另外还有缠着粗粗细细不同颜色棉线的线板儿,有的是随便刮光的木片儿,有的是中间卡腰儿两头儿开着牙子的正正经经的线板儿。孩子们拿绳子翻交的时候,能翻出“牛槽”、“面条儿”、“柴火捆子”、“花线板儿”般般花样,“花线板儿”就是长方形框里打两个X,和那个真的花线板活脱二壳儿。另外还有锥子、剪子、三角形的烙铁,合绳子的陀螺,树叶儿包着带根筷子放在铁勺子里的糨糊,大大小小插在线板上的针,庄稼人的穷日子就靠它们缝缝补补。
活笸箩里最能吸引小娃娃的,还有个小铁锤儿。“小铁锤儿,带铁帽儿,铁鼻子铁眼铁耳朵。”母亲们都是这样教她的孩子亲近这小家什的。
小铁锤儿又称“小斧头儿”,除了敲平鞋底子和鞋帮后面那道合缝的棱儿,铿铿铿给新棉靴砸气眼儿外,它的灵巧可爱,全在砸核桃、砸杏核儿、砸白果、砸大块儿的冰糖上。年轻的母亲逗孩子玩,一只手攥着胖乎乎的小腿儿,一只手拍着肉乎乎的小脚丫儿,一边拍,一边有板有眼地念:
“小斧头儿,
短短把儿,
问问那娃儿叫个啥儿?
叫个黄瓜把儿?
叫个坷垃蛋儿!
扑嚓儿,扑嚓儿两三下儿!”
这个被娇着哄着的孩子,最喜欢干的事儿,当然就是去翻晒妈妈的活笸箩儿了。只要大人一眼看不见,他就哧楞哧楞爬过去,把那些线板儿、铺衬卷儿抖开来搅成一团乱麻,扔得满地都是。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个看上去和他的小脚丫儿有点像,翘起两只小耳朵的“小斧头儿”,一把抓起来,又是摇,又是啃,妈妈看见了,一声惊呼:“我的小祖宗啊!”伸手将小斧头儿夺下,一把抱起撇着嘴就要哭的孩子,心里冬冬跳着,在小家伙的耳朵根儿上一遍儿一遍儿叮嘱:“这可不是你玩的,它会咬人,弄不好在你的小胳膊小腿儿上咬一口,看不疼死了……”
陀螺儿、“日儿”和铁圈儿
从活笸箩儿里发明出来的玩具,除了简简单单一根绳子挽个圈儿翻的“交”,我记得还有两种,一种是陀螺儿,一种是“日儿”。“日儿”原声原味地念应当是“ra”儿,可汉语拼音中没有这个拼法。
“日儿”做起来很简单,随便在活笸箩儿里找个大氅扣儿或是其他大一点儿的扣子,拿一截儿纳鞋底剩下的绳子穿住两个对称的扣眼儿,再把绳子头儿对着打个结。玩的时候将绳子分别套在两个拇指上,扯着一紧一松地扽,想要快些上劲儿,就抡它几圈儿。劲儿上足了,扣子就随着绳子一会儿向里、一会儿向外,飞快地旋转,发出“日儿,日儿”的声音。
“日儿”是女孩子的玩具,男孩子喜欢打陀螺儿、推铁圈儿。陀螺儿这玩意儿我没有考证过,但就它和活笸箩儿里那个合绳子的“陀螺”叫一个名字,就足以证明它也是从活笸箩儿里繁衍出来的。
活笸箩里的陀螺儿有很多种,最正规的是陶瓷彩釉,带有不同的花纹儿。圆圆的上头细,下头粗,中间有个圆孔,安一根筷子粗的木棍儿。合绳子时,盘好绳子盘儿,咬着线头儿捻出一尺多长,在陀螺把儿上绕几圈儿挽个捆儿,一松手放一段儿下去,左手举过头顶,右膝盖轻轻一抬,手跟着上去,把陀螺把儿摁在腿上往后使劲儿一搓,上轻下沉的陀螺就飞快地旋转起来。
兴许是哪个淘气的孩子看见这个旋转不已的物什好玩儿,哭着闹着要,闹得那赶活儿的娘心烦,扬起巴掌给他一下子。孩子受了委屈,跑到爹爹那儿告状,当爹的灵机一动,还是那棍儿,还是那线,还是那陀螺,换个玩法儿得了!习惯了拿扎鞭使唤牲口,立马就想到鞭子,因为要在地上玩,平底陀螺倒过来,改成了带尖儿的玩具陀螺儿。后来越打越精,尖儿上揳个小铁钉,钉盖儿着地,旋转起来光滑又耐磨,陀螺儿就这样发明出来了。
再大些,那孩子的兴趣慢慢转到父亲身上,爹爹去犁地,他一趔趄一趔趄跟在后面趟犁沟儿;爹爹去挑水,他也撵着去,大人只顾看他呢,脚下一绊,哐冬,水桶掉地上散了板,箍桶的铁圈子骨碌碌滚出去好远。那孩子也不看爹爹拧下水的脸,只管跑去抓那铁圈儿……既然这心尖儿宝贝喜欢,干脆找根粗铁丝窝个钩儿,安个扎鞭杆儿,让他推着玩吧……
那个推铁圈儿的孩子就这样离开妈妈的活笸箩儿跑远了,他的世界越来越大,可他再也找不到活笸箩儿里才有的种种乐趣了。
骡车谣
“三岁娃儿,会打铁。
打哩钱,给他爹。
给他爹买个英雄帽儿,
给他妈买双疙瘩靴,
咯咯噔噔上骡车。
到会上,
买个烧饼夹麻糖,
爹呀爹!娘啊娘!
不比您在家纺线强?”
祖母哼唱童谣,抻直腿坐在堂屋门槛上,刚学说话儿的孙子脸朝外坐在她怀里。祖母的下巴紧挨着孙儿柔软的头发毛儿,两只老手攥着两只胖出一兜儿窝的小手,身子一摇一晃,拿小孙儿的右手轻轻地击打着左手心儿。拍一下,小手脖儿上的银镯哗啦一响,逗得这“三岁娃儿”叽叽嘎嘎笑个不停。
童谣里的向往并不高,可那孩子从没见过带篷子挂帘子的高头大骡车。他倒是坐过铁脚车和胶轮马车,不过那不是马拉的,是人曳的。这是个命大的孩子,有一次曳车往春地里送粪,他闹着要坐,爹就把他放在前面的牛屎框上。扒完粪调头往回走的时候,车轱辘被一块砖头弹了一下,猛一颠,孩子摔到了地上,人们一时收不住脚儿,眼看着车轱辘从孩子身上碾过,大人吓出一身冷汗!跑过去抱起来,这儿拍拍,那儿打打,孩子竟安然无恙,只是在虚土地里印出个囫囵的身子印儿。
再大一点儿,下地拾柴、割草,只要碰上顺路的车,他都会缠着牛把儿坐上去。生铁铸成的车轱辘,滚动在高低不平的大路上,咯噔噔,哐当当,带着股沙沙的尘土味儿,颠得人脸上的肉直颤。有时靠着高高的草箩头,有时是柴火捆子,小小的身子裹在浸凉的汗布衫儿里,所有的困乏都被野风刮跑了。真想让这车不紧不慢就这样走下去,永远走不到家才好。他这样想着,闭上眼,那车真的往后退起来。咯噔噔,咯噔噔,过菜园,拐三角坑,到工学田了,到……
“娃子,赶快下车吧,到了!”听见牛把儿喊,睁眼一看,到牛屋院了!
那个三岁娃儿这辈子也坐不了骡车了,他现今在京城里,天天开着
奥迪上下班。不知道裹挟在蝗虫一样的车流里,追着日子紧跑慢跑的间隙,还记不记得咯噔噔滚动在黄土大路上的铁脚儿车。
带窟窿眼儿的木门
大水冲塌了两间草房,我对那个家的记忆模糊成了一片烟雨,唯有东边那扇木门,和一头死在大柳树下的黑驴和它的白蹄子小驴娃儿,至今还有声有息地留在那段永不消逝的光阴里。那扇木门好像没有上漆,要么只是上了一层清漆,在大人胸口高的地方有个窟窿眼儿。光光头没有胡子的爹,一得闲就抱起我对着那扇门一边挤一边念叨:
“挤,挤,挤暖包儿。
挤出来油,炸火烧;
挤出来肠子勒我腰——”
梳一双长辫子的娘,一得闲就靠着那扇木门坐在草墩上做针线活儿。我闹着要吃奶,她就哄我:“出去玩一圈儿,等我这半截绳子纳完就让你吃。”我想了想,一迈腿儿翻过门槛,噔噔噔溜着墙根儿绕房子跑一圈儿,气喘吁吁地一头拱到娘的怀里,说玩够一圈儿了,勾着绳子不让她扎针拔线。她只好放下手里的活儿,把我揽到怀里。西照日头金闪闪的光亮正洒在那扇木门上,照着门上的木纹儿,娘抛出的绳子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