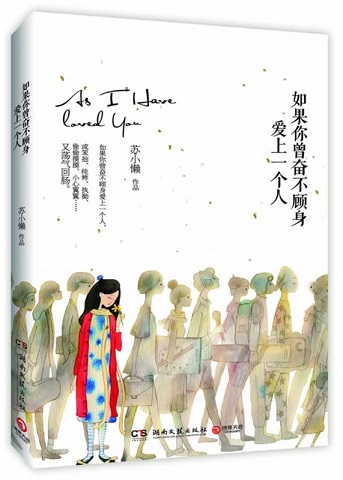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些人在说陈方明的厉害,毁人于无形中,一个皮球踢得那么了无痕迹,那么合乎程序,又那么精确有杀机,让两个最小不拉子的科员去处理一个处长费了心思的宏大构想,这想表达什么?——“对你的示好,我不理”。
下班的时候,我在楼下看到钟处闷声不响地提着一个公文包往车里钻的背影。在初夏的黄昏中,我无限感慨。
7
人事处通知我和方文武等几个年轻人去会议室开会。
蔡副局长坐在那儿。他笑着对我们说,党委会决定为一些处室配备一些处长助理,这主要是为了加快培养年轻人,你们几位,大家都比较看好,这些年做了不少活。
他说,处长助理嘛,也说不上什么官,主要是为了给你们一些锻炼,至于以后,有了这番锻炼,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给你们压担子了。
他瞅着我们,哈哈笑起来,这个单位迟早是你们的,这个天下也迟早是你们的,要给你们压担子……
我回到办公室,还想着他像毛泽东主席一样的语言。程珊珊他们知道这事了,要我请客。我看见卓立有点难看的脸色,就赶紧说,请个屁啊,也不是个什么喜事,我也搞不懂这个助理是干啥的。
程珊珊说,你也真是的,要你搞懂干吗?这“助理”虽然还不是副科,但是个逗号,说明还有下文的希望,说明你进入领导的视线啦。
8
这楼里,许多人也在谈论突然而至的“助理”之事。
一些人在问,这是哪门子的头衍,这头衍是用来干什么的?一些人分析:上一任老虞,喜欢大派官帽,结果现在正科、副科位置都占满了,编制用完了,轮到蔡这里,他手里没小乌纱帽的余额了,他用什么去吸引别人跟着他啊,所以,他现在只有推出“助理”这个创意了。
一些人说,这些助理,是革命小将,他现在要用革命小将对付余孽。
分析完“助理”的逻辑,接着就是琢磨我们这几个为什么成了“助理”,或者说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几个成了革命小将,或我们是如何能够成为革命小将的?
于是,我就面对了自“林娜事件”之后自己再次被人议论的窘境。
他们说,老蔡是记着小贺的功的,你知道吗,这事的来龙去脉最初是小贺传出来的,老蔡是记功的……
这些言语飘到我的耳朵里,我真的不想去上这个班了,我甚至连中午去食堂吃饭都有了心理障碍。
即使我不想上班,流言还是顽强地传过来,这次说的与林娜有关。
他们说,他们升官的升官,玩牌的玩牌,林娜呢,林娜呢,被搁在资料室没人理了,用过就没人理了,还成了被看热闹的笑话,她这根改革的导火线倒是够冤的,导火线成了牺牲品。
他们感叹,都是这样的,有点姿色的女人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大都是这样成牺牲品的。
9
我假装还书,悄悄去资料室看林娜。
每当我想起她心里不知在怎么看待我时,我就不舒服。我进了资料室,见林娜耳朵里塞了只耳机,在看书。
我大声说,林娜。
她看了我一眼,继续低头看书。
我对她说,林娜,还书。
她把书收回,放在桌边,继续看书。她也没摘耳机。我对她大声说,林娜你这阵在忙啥那件事说真的我真的特后悔其实关我屁事算我多嘴……
她自顾看书,没睬我,犯倔的气息仿佛正从她头发里向上蒸腾着,这让我产生她确实是牺牲品的强烈感觉。
我告诉她是我多嘴,她的事该不该张扬得由她自己先做主,她的尊严怎么维护也应该由她自己先做决定,别人横插一杠做尽文章最后伤了是她,这事是我惹的我没想到会这样算我多嘴……
她接起头,眼里有一丝尖刻的笑,她说,那么你现在就别多嘴了,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事,我最近和朋友合开的那家店要开张了,一忙,我可能就要走了。
我说,你也要走了?
她低头看书,她说,我不想陪你们玩了。
10
我刚回到办公室,陈方明就打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
我走进他的房间,他说,祝贺祝贺,这次上了助理。
他说刚才蔡副局长和他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去综合处,下个星期就去。
天哪,去综合处,又是去综合处,居然让我去做钟处的助理!
我说,我不去,我也不想当这个助理了,我这阵子心里很烦,很没劲。我说,如果你不方便为我说,我自己去和蔡局说,我不太适合当助理。
陈方明温和地看着我,说,你得帮帮我,那边有点协调不起来,你过去,是因为我相信你的。
我说,我很烦,因为很多东西传来传去,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们别烦我好不好。
他告诉我别总是在乎别人传什么,别人永远是要说闲话的。工作本来就是很烦心的,正因为烦心所以需要你去做啊。他说,你帮帮我吧。
11
我去了综合处。
我又坐在了三年前我坐过的那个位子上。
钟处给我的脸色,让我想起那一年的蒋志。
我想,别看着我烦,我又不想来,关我屁事,我又不想干什么,暂时也没野心,钟处你爱谁谁吧,不给我好脸色我不在乎。
一个星期下来,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如果把自己当一个科员去写调查稿,那么那些同事会对我有想法,他们会觉得你是助理了,还要抢他们的工分;但如果不写,这么晃悠着,别的同事也会有想法,他们会觉得你当了个助理就不干活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去问钟处。
这时钟处自己来找我了,他拿了一张考勤表,给我看了一下。细算账,这是他一惯的风格。他说,你是助理了,这周每天迟到,星期一迟到了10分钟,星期二迟到了7分钟,星期三倒好迟到了15分钟……原来我也不想说你,但不说你,别人会看你的样,现在的年轻人不知怎么这样,这次都提拔你了,你怎么反倒没精神了?
他说,我这份纪录交给了人事处,因为,我现在吃不消多说你,但我不说你,别人会说我,这个月奖金怎么算,让人事处决定吧。
我很奇怪,自己这次居然没不高兴。
我告诉他,真是不好意思,这个星期迟到,是因为我天天晚上在医院陪丁宁,他病得很厉害,上周胃里动了刀,你知道吗?
钟处说,什么病呀?
我说,不是什么好病,他家人为了瞒他,所以也瞒着别人。
12
这一周,每一个晚上,我确实在医院里陪丁宁,因为她老婆一个人陪不过来,身边还有一个2岁的儿子晚上要管。她背地里哭伤了自己,因为诊断他是胃癌。看着他一家人眼下愁苦的模样,我就让她白天陪,晚上我来。
他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我们对他说好的,但我估计他心里可能有数。
他说,你们别骗我。
他说,怎么你来守夜,怎么好意思让你来守?
我说,你啊,现在是正科级了,我要巴结了,你别赶我走。
他有点高兴。他说,我想可能再过两个星期,我就可以出院了。
我看他好像在观察我的表情,我赶紧装没在意,和他说别的话题。在医院的这些夜晚,我们不太扯单位的事,因为我们过去扯得太多了,现在,在飘着药水气息的病房里,我们回忆得最多的却是当初我们刚进单位时那个阶段的事,一块出去泡妞,一块周末去大学舞厅跳舞,长假时一块去南京玩,每天晚上坐在集体宿舍的床上胡扯政治、股票以及做点什么可以挣钱……
他说,那时候真好玩,刚毕业的那几年最好玩了,人这一辈子好玩的时间不是太多,中国人好玩的时间真是太短了,读书的时候,考试那么苦,不觉得好玩;工作最初的那几年,自己没什么压力,也没人当你回事,也没人打你主意,是最好玩的,但一过五年就不好玩了,什么滋味都来了,就不好玩了,中国人好玩的时间真是不长啊。
每天夜里当他熟睡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边上打个瞌睡,许多人以为我是他的弟弟,我想,一年前,我们还是互相提防的对手,再早两年,我们挤在一个办公室像两只好斗的小公鸡,人怎么会这样的?也可能挤在一个办公室里空间太挤了,拥挤感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压力,让人与人产生心狠和紧张?而现在,在医院,我想着他以前“在马岭镇打电话给钟处说我不是”、“新官司上任在我面前找感觉”、“在领导面前巴结得像穿花蝴蝶”等等不是,都像羽毛一样轻飘起来,我对睡梦中的他早已没了怨感……
我发现,在病痛的迷糊中,他好像总在惦记着家里的一些东西,比如冰箱里的面条、酒、面包、花生、山核桃什么的有没有过期。他来自农家,我理解他。物质在一代代人心里,可能从来就占据着巨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的逼仄,就像办公室的拥挤一样,也常会让人彼此焦虑和不善良。面对不知病情的他,面对睡梦中他苍白陌生的脸,我常常感叹不息。
13
我坐在办公室。钟处给我的脸色依旧,但我好像对此已迟钝了。
陈芳菲说我怎么总是在发呆。我说,没有呀,我没觉得,你们千万别觉得我在打什么算盘。
陈芳菲叫起了,哟,我可没这样觉得。
正说话间,钟处进来了,说,开会。
这个会议是各部门对中层领导进行民主测评,测评的对象是处长钟处和副科长陈芳菲等几个。
测评表由我这个助理分了一圈,每人一份,无计名填写。
这表要填的内容很细,许多人在写着,我听到了一些声音,新来的大学生汤海生在问“这格填什么这格填什么”。瞧他那认真的模样,我让他随便填。
大家填完,我把表收起来,放在桌边。我想等一会儿到楼上人事处去交掉。没想到钟处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他对我说要看一下我们部门填的测评。我愣了一下,说,这可能不行吧。
他的眼里我有熟悉的强势,他盯着我说,怎么不行,我是这个部门的处长,我得知道第一手的信息,这对工作、对了解部门同志的想法是有用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的强势近来常让我遏制不住自己的犯倔。我说,那我得问一下人事处的同志,这可不可以。
我就拎起电话打过去。钟处在一旁的脸色很难看,所以我没多看他。人事处的裘处长说,这不行的。
我放下电话。对他说,他们不同意。
我往外走,我知道他愤怒的目光停在我的背上。其实,我今天原本没想伤他,我在这里发倔只是因为心烦,也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照顾丁宁没睡好,所以看着腻腻歪歪的事儿就想发火,就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当然,钟处肯定不这么想,他肯定认为我是谁谁的革命小将,他认定我翅膀硬了,由他去想,我烦了你就别来理我。
人事处打电话来找我,要我上楼想了解一下刚才这事。我说,我不来了,反正他是想看。
人事处长有点犯难,他说,是蔡局长的意思,要了解。我说,有什么好了解的,他又没看成,怎么,你们还要弄得像真的似的。
后来人事处还是找钟处上去谈了谈。钟处下楼后,脸色发青。我看着他进办公室的背影,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觉得我有点犯傻,我对着桌子底下踢了一脚,我记得自己重返综合处第一天就提醒过自己千万别和他冲撞,因为我们撞得头破血流,偷着乐的是蔡局和陈方明。今天我一失控,就真的成了革命小将。
14
与白天在办公室的烦闷相比,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医院。
这些天,我向单位打了招呼,请了几天假在医院陪服丁宁。单位里的人说我思想好。汤丽娟托我把她编的一顶线帽带给丁宁,她说,他化疗用得着。她说,以前看不出你们这么哥们。
我想,我思想好不好天知道,我只觉得坐在病房里和他聊聊天,比呆在办公室内和钟处犯冲好,在这里,四下安静,能让我慢下来,坐在丁宁的边上,帮他们夫妻一把,让我觉得自己这阵子还有些用。
丁宁已经开始化疗了。他的头发没了。他戴着汤丽娟的帽子,在床上显得很安祥。他说,这些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时候的事。
他说,我小时候在田野里放牛,七八岁的时候,有一阵突然明白了人有一天会死的,心里对死亡充满了恐慌,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阶段,是不是人都有这么一个时期?有一天我越想越怕,就坐在烟草地里哭泣,结果牛跑掉了,我一边哭一边在田野里找牛,一边害怕遥远的死亡一边害怕回家……他虚弱地笑着对我说,是不是人只有在童年时代或者快死的时候才特别关心生死问题?平时忙忙碌碌,是无暇顾及这些的,小时候大人对我的恐惧总是嗤之以鼻,事实上我长大以后也很少想到死亡,而是像多数农家子弟一样,想着锦衣还乡的戏剧性……
化疗消耗了他的体力,他的声音从没像现在这样缓慢,他让我觉得很生疏。我们在一幢楼里呆了10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觉得他陌生,也好久没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在静下来。
他总是想从我们嘴里探出自己的时日预计,他笑着说,医生告诉我要慢下来,慢下来,我也想让自己慢下来……
那天我离开医院的时候,路过中央广场,在人潮中,我突然听到了丁宁少年时代对死亡的哭泣。
15
我跑回单位,去人事处。
我问他们, “首席调研员”的聘书都发下来了,但为什么丁宁的“调研主任”还没发啊?
他们就冲着我笑,他们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丁宁得癌了呀。
我说,但他还活着。
他们说他们也没办法,哪有任命得癌病的。
我说,以前分房子,只要退休员工人还活着,还有一口气,也是要分给他的,现在丁宁还活着,不就是发一张纸吗?
他们对着我笑个不停,他们说,你别缠了。
我一遍遍地去找人事处,我说,不就是一张纸吗,有什么好那么顶真的,发给我吧,我拿去给他看一眼,就拿来还给你们,不就得了。
他们看我急的样子,笑坏了,他们说小贺你怎么这么好玩。
我悄悄找人事处副处长夏燕,我说,你悄悄给我一张不就得了,我拿去给他看看,人家好歹想了多少年了,人家好歹也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是个安慰,也是个交待。
夏燕瞅着我说,是的是的,我理解的,但这事我也做不了主的,他得的是癌,发给他,别人看问题可能不这么看。
16
有一天下午,我在医院,被钟处叫回单位,说要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