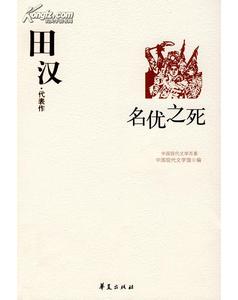田汉文集-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月光
有的人当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总爱喝酒,说因此可以忘记他的痛苦。但以他的经验,却不然,他越喝酒,心里越加明白。内心的悲哀不独不能因酒支吾过。而且因为酒的力量把妨碍悲哀之发泄的种种的顾虑全除去了,反显出他真正的姿态来。
他到这异乡的上海生活以来,不知不觉又过了两个节了。七月七刚过了,又是八月中秋,好快的日子!他的弟弟买了许多桂花来插在瓶里,摆在靠墙放置的桌上。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弟弟也懂得色调的配合。他因嫌白壁太单调了,不足以显出桂花的好处来,便借邻居叶君的一块紫色的花布钉在墙上,那金黄的桂花得了紫色的衬托果然越加夺目,萧索的寓楼中有了她发散出来的芳香,顿时温馨了许多。因为今晚是八月节,清澄皎洁的月光不可辜负。和他同居的 E 君爱喝几杯,打了许多酒来,晚间便大吃大喝,他约莫也喝了斤把花雕,正如上面说的,将欲销愁,而愁的形态像雨过天晴的月色一样更加明显起来,他便倒在床上睡了。E君与他弟弟邀他到街头步月,他没有应他们,他们以为他睡着了,便不勉强他。他们去后,他起来拿起笔来要写一点东西,但是写不了,头好象有一点痛,便熄了电灯,依然睡在床上,电灯一黑,那清圆的好月立刻趁着她那放射的银线由窗子里跳进他房里来,吻着他的床。他此时的心里虽因喝了酒愈加明白,但在他眼里的月的姿态却模糊起来了。
“S 妹”他喊她一声,她不答应,知道她睡着了。他把她的被盖好,起来放好帐子,房里虽然有一盏美孚灯,但不足以抵御月光的侵入。他走到书桌旁边坐下了,桌上还放着栈房里老板送来的月饼,他虽不饥,无聊地也拿着吃了,一面吃一面痴痴的抬头望着窗外,真是玉宇无尘,晶光似濯。他想此时若能同她一块儿去步月是何等幸福,偏她又一病至此。又念刚回去的慈母、幼儿,今晚不知在哪里过节,他一边想,一边听着帐子里的呼吸,也还均匀,似乎一时不至于醒来。他便慢漫的出了房门,走到院子里,满地银光,真如积水空明。由院子直走,出了大门便是扬子江边了,由堤边一带垂杨荫里望那扬子江时,滚滚江涛映在月光之中,就像无数人鱼在清宵浴舞,他独自一人伫立多时,渐渐觉得身上穿的单衫挡不住午夜的江风,又恐怕那卧病在异乡客舍中的可怜的人要醒了,急忙拭于眼中因江风送来的水珠,慢馒地踱回房里去了——这是他的去年今夜。
这时是他和她回上海的第一年。他们和他的朋友 Z 君夫妇住在哈同花园后面民厚南里的一家楼上。这天晚上也是八月中秋, Z 君和另一朋友邀他们俩同去步月,她穿着红色的毛衣同他们出去。从静安寺路转到赫德路,又转到福煦路,就是围着民厚里打了一个圈圈,他们便和 Z 君等分开了,他们沿着古拔路,在丰茂的白杨树荫下携手徐行,低声地谈着他们谈不完的心曲。那时的古拔路一边是洋房子,一边却是一条小港,小港的那边是几畦菜园,还有一座有栏杆的小桥,桥头有几株垂杨低低地拂着桥栏,桥下水虽不流,却有浓绿的浮萍,浮萍里还偶然伸出一两朵鲜艳的水仙花。靠着菜园那边,还有一带芦苇。参差有致。他们自从发现了这块地方,常常爱到这里来散步。今晚他们因想这块具备了长芦垂柳碧水小桥的地方在明月之中不知更增几许姿态。所以特来领略这美丽的自然。果然不使他们失望,柳、芦、桥、水、浮萍、水仙都好像特作新妆迎接他们,他们站在桥头受着月光的祝福,他觉得这种情境很有画意,回家后他便画了几张小桥观月图分送他的好友。
他回忆了去年和前年今日的情景,又联想到今夜的故乡,母亲和孩子在乡里过节,母亲一定思念她在外面的儿子,孩子虽小也一定想念他在外面的父亲,但他一定以为他的妈妈也同他的爸爸—起在上海,他哪里知道今晚的月光,不能照到他妈妈的脸上,只能照着她坟上的青草呢!
可怜一样团 月,
半照孤坟半照人。
他还没有念完这两句诗,便痛哭得在床上打滚了。
上面这几段东西是他昨晚写的。因为都是月夜的回忆,他题之曰“月光”。不过他今早起来,照着他床上的不是“凄凉的月光”,却是和暖的阳光。他昨夜的泪痕在阳光中一忽儿 都 晒干了。他以后不敢再在月光底下回忆,不敢再于佳节良辰喝酒,不敢再惹起他的旧痛。他年纪还不大,还想忍着痛苦做些事,这也是她所希望于他的,他现在与惠特曼同样要求着“赫耀而沉默的太阳”,他与惠特曼同样唱着《大道之歌》“从此以后,他不再呜咽了,不再因循了,他什么都不要,他要勇敢地、专心致志地登他的大道!”
作于一九二六年
杏姑娘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西施之能由浣沙溪畔使“吴王愁吴宫秋”,也还得感谢范蠡之拔识。不然天下艳色之埋没随百草者,岂在少数。近世电影业发达,在世界的“圣林”好莱坞被歌颂为明星的,真是宫室车马拟于王侯,一举一动悉为世界之视听所聚。曼莉薛馥夫妇之游欧,其所受热烈的欢迎过于威尔逊。华伦铁洛死后之哀荣非墨索里尼所能望,但他们之能由微贱致身于后来的地位,亦有幸有不幸。因为人的生命有限,青春一去,永不能还,男子还不大要紧,女子的“真的生命”较男子尤短,在他们那蔷薇花般的含苞末吐以至盛开的时候不能得一机会发挥她们的真的生命,及至盛期一过,谁复有多情的观众,拾春泥中的落花,想象如那招展枝头受好鸟赞歌时代的仙姿曼态呢?
这是我在由《获虎之夜》介绍过的仙姑岭下的事。我们家里这时已分家了。我的祖父住在隔仙姑岭很远的田家 。我们兄弟时常带些山里的东西像红薯之类,或挑一担干柴去孝敬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时常扶着拐杖由路上的铺里秤几斤肉或是买些糖果来给我们吃,因为他老人家是最爱我们的。一次我又奉母亲之命去探望祖父,拿着一根自己在山里砍的棒,口里唱着自己最得意的“勒马扬鞭登古道……”沿一条溪水而行,走到梁家庄的旁边。溪水较宽,溪的对面绿杨之外,还有几株梁家护庄的大树。有一条小路由梁家的侧门通过菜圃蜿蜒到溪边,与搭在水上的石跳板相衔接。依依的柳绿,微风吹来低拂跳凳端,这一幅画图似的田园风光,正位于我到祖父家必经的路上,它曾使我少年的心跃动过多回了。可是没有比今天更跃动得厉害!平日爱在柳绿中穿梭似地跳跃歌唱的黄茑,现却在枝头呆然木立,连唱歌的功夫都没有了。因为今天那里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正在石跳上洗衣。柳绿微吻着她那漆黑的鬓缘,衣角被风吹动了,可以窥见她那淡红的衬袄,由那高卷袖子的素腕,可以想象她的莹洁的肌肤,她那浣倦的姿态和她那生命流动的曲线,使人为之陶醉。她娇羞地斜靠在石跳上,一双纤足侧映在微微波动的水中随波荡漾。她是当时我们家乡十里内外的一个有名的美人,叫梁家七姑娘。据说她父亲择婿甚苛,首先要有“家屋”(就是要有财产)。挑选至今她已二十岁了,还没有看人家。你不曾听见侧门里出来的那个女人喊她做七姑娘么?她回答那女人的话的时候,那银铃似的声音清脆悦耳是何等令闻者为之心旷神怡啊!
前年因送漱瑜回湘养病,才有到仙姑岭下重游旧地的机会。当日唱“勒马扬鞭”的古道上仍然绿草如茵,梁家庄旁的小溪依然潺潺缓缓唱着旧日的清歌,柳丝儿拂着石桥,黄茑儿穿梭似的飞跃高啭,可是当年那斜跪在石跳上洗衣的人早已嫁了,早已寡了,早已又嫁了!我在一个亲戚家里遇见了七姑娘,她已变成一个愁苦的中年妇人,梳一个小小的巴巴头,缺了一个门牙,听说是被丈夫打脱的,脚是放得不中不西,只有她那紧蹙的双蛾还依稀留着美人的痕迹。总之,这个“天之瑰宝”算是莫名其妙的被葬送了,埋没了,坑杀了!
前年曾因凭吊废墟而悲,也曾因发见新地而喜,新地者杏姑娘也!在东京曾看过一部影片叫《路旁之花》,杏姑娘是真真实实的“路旁之花”!
由长沙省城到我们乡里足有七十多里路。那时我的漱渝在乡里养病。我一直在乡下看护她的病,后因有事上城公干,在省城接到漱瑜病势转剧的信,是阴历十二月十九日的事。因为老友皮君也要下乡,我邀他同行。前一天垂暮,岳麓山头的夕阳把湘江映得火也似的红,我们都庆喜明天有个好天气。到第二天早晨从床上向外面一望,天空和我的心里一般的暗淡,窗上的玻璃都含着雨点,有的还泪珠般的一颗颗直流。我想起漱瑜的病状,当我动身的时候颇为平稳,不应该忽然转剧,光景是她想我回去来吓我的吧!死?决不会!我不能作此想。但我的泪珠早染湿了人家的枕头了。因为漱瑜爱吃雪里红,我跑到南货店里买了一大把雪里红放在篮子里,走到皮君寓所与他会齐,扎起棉袍子的前后襟,撑起雨伞,冒着寒风冷雨,登我们的归路,我想阴历今年是不上城的了,我可以招扶漱瑜,陪陪慈祥恺悌的外祖父,看看书,过年的时候还可玩玩多年不曾玩过的龙灯,而且篮子里有的是雪里红,漱瑜明天的早餐一定比平常要有味一点了。咳!对于运命盲目的我,哪里知道我那可怜的漱瑜竟于我抵家的那晚弃我而去呢!不知道悲惨的命运在那里等着的我走到离城十五里的月湖堤,见两旁被前次大水冲平的坟茔,为状甚惨,因对皮君说:
“达三!我出一个对子请你对。”
“你说呀。”
“‘白骨黄泥地’!”
“‘轻风细雨天!’好不好?”
“太平常了,地何必一定对天,你看,我们快要到张家堆子了。张家堆子的杏姑娘长得很标致,就以她为题,对个‘蛾眉皓齿人’不好吗?”
“果然好!可是……。
达三说到这里好像想起”什么事,忽然不说了。后来他对我叹道:“不料那天那个对子竟成了谶语,你想‘白骨黄泥地,蛾眉皓齿人’联成一句,成了什么意思?”我听了也为之悚然!
在那伤心的一天──我一生最大的悲哀的一天的数小时以前,我和达三又在张家堆子茶店里与我所谓真正的“路旁之花”谈了好一阵。我的笔太沉重了,不能再写下去。我只把二舅交我的一封信照记忆所及,记在下面,也同样可以表达我对杏姑娘的命运的同情。
寿昌: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急于要找女明星,我在昨日上午便和一位朋友同到月湖堤去了一趟。月湖堤上的行人,背着包袱的,推着车子的,挑着担子的,坐着轿子的,形形色色,匆匆忙忙,来的要尝尝都市的繁华,去的要重领家庭的乐趣。他们对于月湖堤上的要求,至多不过喝一杯茶,换一双草鞋,或是下轿来,伸一伸腰,暖一暖脚,风流一点的少年也不过嗑着瓜子与那娇声浪态的茶铺里的“魔女”交换那一瞬间的情话:
“请进来喝杯茶啊,何必这样忙呢?”
“少陪啊,回头再来坐吧。”
这就是月湖堤上的情史的全部了。谁像我们把月湖当作浣纱溪学访西施的范蠡呢?
快要到张家堆子了,我们的精神陡然紧张起来,分明是要到她那里坐,却故意和其他无心的行客一样头也不回的走过去,但是杏姑娘锐敏的眼晴早发现我了。
“蒋先生!下乡去吗?吃杯茶着啥!坐下着啥!”
“啊!杏姑娘,好久没有见。”
“真是好久没有看见你们打这里过身呢,你们都好吗?”
“除开我依然‘打流’之外,他们总算都还好。”
我们便趁这机会走进了茶铺。她见我们停了步,便连忙掇椅子给我们坐。那双手虽然还白嫩,可是指头都皱了。月湖堤上的风,你是知道的,何况又挟着这样的春寒,见她在冷水钵子中洗杯子替我们倒茶,觉得这杯茶来得非常辛苦。她依然梳着辫子,围着一条紫色的围巾。我赞道:
杏姑娘,你那条围巾真正漂亮呀!”
她一面倒茶,一面用她那双妩媚的眼睛望着我微笑道:
“晓得不好啊,不过这里冷得太厉害了,实在非有一条围巾不可,这是我上个月托人在城里买的呢。”
我本想说:“那么杏姑娘何苦在这样的地方喝西北风,何不到上海去当明星呢?”一想这话可能说得太急率了,何况在她的眼光中,觉得当电影女演员的不见得比茶铺里的姑娘高尚呢!
她照例地招呼了客人之后,又坐下来和我们谈话了。
“蒋先生,你今天下乡去?”
“不是,我替田先生找明星去。”
“田先生,不是那天死了太太的田先生吗?可怜他去年十二月和皮先生一块下乡的那天,正是他太太死的那天呢!他那人真怪,有一次走这里过身的时候,他同他的弟弟挑着一个重担子,走得气喘喘的,听说挑到石灰嘴才发脚,我端些瓜子花生给他吃,他一点也不吃,只喝了一杯茶,我以为他舍不得多给茶钱,可不料他走的时候,给的比别人还多。第二次他坐轿子经过这里也在我们这里坐,这回我妈妈端了许多东西款待他,他也不过给那么多钱。蒋先生!怎么你那些朋友,都是些怪人呢?”
不错,我们都是些怪人,都是些畸形人!我们这些为社会所误解所轻蔑的人却被月湖堤上茶店的姑娘称之为怪人,这是何等悲痛的事!后来我便谈起你的近况了,讲到你要我替你找明星,她很感兴趣地问我道:
“蒋先生,你说替田先生找明星,明星到底是什么?我们乡里有明星吗?”
我不说“演电影的女戏子”而说“明星”者,原是要她觉得“明星”这东西比茶店里的姑娘高贵得多。但她逼着我解释的时候,我又为难了,我只好仍是给她一个莫名其妙。
“明星是一种从事电影工作的艺术家,英国话叫做Star,就是天上的明星的意思。”
“那么,田先生托你到长沙来找天上的星吗?那怎么好找呢?”
“不是讲天上的,也还是指我们人,指那长的很漂亮的人,尤其是姑娘们。”
“找到上海去又怎么样呢?”
“譬如我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