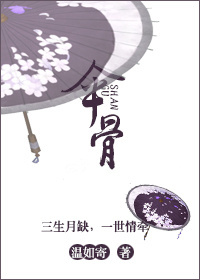红纸伞-第5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无数的林子长起来了,无数的女子接踵而来。
现在又有了培育奥地利铁杉的成功,有了新的一群初出茅庐的女孩子,她们用隔年陈种培育出了高品质的冷杉树苗。
当初第一代营林女工是老三届知青,她们哺育了第一批树种。在这最初的小苗里,蕴涵了他们对于生命的全部的想法。如今小苗已经参天,在溪水坪附近的林地里茁壮成长;
第二代女工来自西安城里的一次招工;
第三、第四代都是伐木工人的后代;
第五代营林女工平均年龄只有19岁,大都是林校毕业生,年龄稍大的来自农林学院。
由点种到发芽,幼苗在苗床中长至二、三寸高,三年后移入大田,长够两年再栽入林地,安全度过“保护期”——林木成材的周期是120年。
百年之后谁能看见当初育苗的女子?
谁能体会营林姑娘的心情?
百年之后,当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在新的成林里采伐原木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读懂湮没在树木年轮里的青春?
父亲那一代人为之努力一生的森林,已经开采到了极限。
林区小镇,在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已是穷途末路。
只有十八里苗圃的营林姑娘是活泼的,健康的,英姿飒爽的。
从她们的口中已无法访问到早年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她们已不记得这里有没有“秋晓”这个人。她们喜欢郭富城和黎明,偶尔伤感起来她们会强迫自己去看林语堂的《品味人生》,但她们的愁伤只是夏日午后的流云,来时一阵风,去时一场雨。
她们是没有过去的。
假若我真要在她们的身上挖掘过去,实在是很傻的一件事。
她们怎么能够知道这片森林实际上就是我的天堂。
在我对天堂的向往与追逐中,我心中的天堂已经失落。
我回不到天堂里去了。
我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我的樱桃谷,我的樱桃谷的木屋,难道也湮没在沧桑过后的绝灭中去了吗?
5。火凤凰
以溪水坪为大本营,兵分两路,采访忙碌而紧张。
在采育七队,高空索道正在放料,我们抢拍了一组绞盘机旋转、木料从几百米的山顶吊起来、经过高空运输定点投放在山脚下的大卡车上的惊险镜头,以便用做将来文稿的压题图片。顺便还完成了一篇《一个伐木工的工资》的专题采访。
在勘察设计队,王憨对那些“一年到头住帐篷,每天疾走70公里,勘察森林资源,设计采伐方案,每隔120米设置一个观测点,动作稍慢就得露天宿营”的森林勘察队员的生活发生浓厚兴趣。勘察队员每天背着仪器奔走山涧,一个点一个点地测量树种、胸径、土壤等资料,他们探测到的资料是森林保护与再生的绝对依据。王憨从中体验出了另一种生命风情与人生况味,而后完成的那一篇图文并茂的《每天走六七十公里的人们》的专稿,既讴歌了火热而平凡的生活,又用新视觉、新角度、反思维地提出了另一种保护森林的观点:“森林是一种有生命的动态群落。一片森林成材以后,如果长时间不去开采,木材蓄积量倒有可能出现负增长,老树会空心,腐朽而死。所以并不是不采伐才是保护森林。”
另外两个女编辑也是采访的快枪手,神不知鬼不觉就从工会赵主席那里挖掘并连夜赶出采访稿《狩猎黑熊的那个惊人的夜晚》,讲述了在挺进大森林的初期发生在采伐队的惨烈故事:小河边,涧溪下,一群可爱的黑熊在无忧无虑地喝水,嬉戏,一杆猎枪伸过来,打死了最小的一只熊宝宝。几位操刀的快手极利索地剥下熊皮钉在门墙上,炉火通红煮食熊肉,人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突然,熊妈妈来了,凄惨的哭嗥,撕心裂肺的吼叫,熊妈妈向无知的猎人索要自己的孩子。暗淡的星光下,熊妈妈撞击每一堵墙,每一扇窗户,它在院子里发疯地奔跑,在周围的林地摧毁树苗,在屋后的庄稼地里肆意践踏,夜夜哭声不断,夜夜复仇不止——熊妈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采伐队只得挪到另一个地方去住。惊险刺激的描述,寓言一般的诠释,极有深度地提出了“人与动物的亲和”这样一个人性化的环保主题,呼吁并提醒:法制昏聩的人们啊,及早觉醒吧!
采访很顺利,大家情绪高涨,我心里的石头却总也落不到地。
我从工作状态里感受到的那份快乐与充实,在工作将要告一段落的时候,渐渐变做无端的惶恐和不安。
最后一天的时间是属于随行美编和摄影记者的。他们要拍一组《有奖竟猜》的图片,就像《正大综艺》一样,既体现读者参与性,又紧扣主题强化“绿色行动”的思想性。
主编随身就带着新一期杂志的稿件,难得清闲,就静坐一隅,改错词病句,改标题华笔,津津乐道于她那极具权威性的后期包装。
王憨在整理采访笔记。
芭紫和秀子跟另一支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实习队去采集生物标本。
只有我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带着另一种非同寻常的使命。
工作时我是快乐的,工作完了快乐就走了。
回到樱桃谷却需要勇气和决心。
而我似乎到这时候才知道,我所缺少的既不是勇气,更不是决心。是什么?
“你知道樱桃谷吗?”我曾问过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我问每一个被我采访过的人——宣传科的马科长,工会赵主席,采育七队的张队长,森林勘察设计队的李队长,甚至林区小学已经退休的老校长,甚至林区小商店当年卖散酒的老头儿:“你知道樱桃谷吗?你知道在溪水坪的西边,沿着溪水奔流的方向,有一个叫樱桃谷的地方吗?请你回忆一下,在十四年前,198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樱桃谷,在那个守林人的木屋前,一棵歪脖子树下,上吊了。”
没有人回答我。
或者不愿意,或者不知道。
人们啊,难道如此淡漠,如此健忘?
樱桃谷的那一场生生死死的故事,尘叔和秋晓,父亲和他的情人的故事,真的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哪怕变做今天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哪怕变做面目全非的神秘传闻,也是对我的一种慰籍。
我终于知道,苦难只是相对于苦难者本身才具有苦难的涵义,而冷眼旁观的人们,永远不会有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记忆。
后来,有一个人总算想起来了:“哎哟,樱桃谷呀,不就是发生火灾的那个地方吗?”他告诉我,1981年9月的一天夜里,樱桃谷突起一场大火,先从哪座木屋烧起,后来整个屋后的林子也窜起了火苗,大火烧毁了一个美丽女人的脸,烧坏了一个守林人的一双腿。他说:“关于这场大火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是9月,还没到防火期,夏秋之交也没有雷击和闪电,烧得邪乎。”
呆住了。
完全呆住了!
好像记忆里早就彩排过的一幕戏终于上演。
那场大火是真的烧起来了。
从十四年前的记忆中烧起来,一直烧到我的回归。
而我在那一年离别樱桃谷的前夜,分明梦见了这一切——那一夜的樱桃谷,火光冲天,我的逃离好像是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在梦中我还看见我的弟弟商彤——呵,商彤!
“还有一个小孩子呐!”我脱口而出:“他在哪儿?是不是他?是他放了那把火?”
那个人再也不愿意讲下去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去问猎户老吴头吧。”
老吴头我知道。
他是整个林区独一无二的百发百中的老猎户,父亲那一套用“千斤闸”捕猎野麂的技巧就是跟老吴头学的。父亲和他是有酒同喝有肉同吃的交情。现在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猎户人家和各种猎具已是昨日风景。老吴头在溪水坪东边一个背风向阳的山谷里养了一群梅花鹿,靠出售鹿茸过活。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他的小鹿们喂水喝。
“你知道樱桃谷吗?你知道十四年前的那场火灾吗?你知道是谁放的火吗?你知道那里的人现在在哪里吗?”
老吴头饱经风霜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悸,好像我惊动了他心底某一处绝不愿被人碰触的隐痛:“你问这干什么?你还嫌那可怜的一家人不够栖惶吗?”老吴头说:“好好的一家人,伤的伤,残的残,死的死,散的散,没有喽!”
最不愿听人说生死,最不愿听人讲苦难,最不想知道父亲遭遇不测。
可是这一切,偏偏让这个老吴头给说出来了:“他们就那样被人从火里给救了出来,女人烧坏了脸,男人烧断了腿,可是他们没有哭,因为他们赢了——那么大的火也没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就觉着自己还是幸运,还是幸福的——他们相信人活一口气,只要活着,只要还有这一口气,他们就要在一起——在一起,他们就会有一切。”
呵,父亲!
呵,母亲!
闭上眼睛我就看见你们在受难。
火焰熊熊,煎熬着儿子的心;
烧天烧地,焚烧着儿子的身。
如果经历了这一切,你们才终于拥有了幸福,这幸福也太奢侈了;
如果付出了这一切,你们才终于获取了爱情,这爱情也太昂贵了。
老吴头说:“他们的行为感动了周围的人,都说他们是一对火凤凰,火凤凰!火凤凰!!一对火凤凰哦!!!”
火凤凰?!
多么形象的比喻!
我可怜的双亲啊!
究竟是涅槃之上浴火新生的凤凰,还是萧史弄玉乘着凤凰嬴台飞去?
跨凤乘凰客,牵牛织女星——好不惘然!
老吴头的声音像是噎在喉管里了:“好多人都去祝贺他们的新生,他们住院的时候,医院里里外外都挤满了看望的人,医生护士都对他们特殊照顾,并免去了一大笔治疗费。人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出院了就轰轰烈烈办个喜事,堂堂正正地过日子。他们也真等到了这一天,终于在樱桃谷重新置了家。男人没了腿,女人就用手推车推着他走;女人的眼睛看不清东西,男人就用自己的眼睛给她指路,每日晚饭后他们就在从前小屋前的山道上散步,她推着他,他给她说着话;她唱《李彗娘》,他就附和着给她打拍子,敲梆子,用嘴哼哼着拉过门,两个人总是乐呵呵地,好像他们从来就没有损失什么,好像一切都跟从前一个样样。一晃就过了好多年!”
一晃?!
一晃是多少年?
我可怜的双亲呀!
为什么从不告诉儿子?
为什么儿子一点都不知道?
在你们的“一晃”里,儿子读完了初中,上完了高中,大学毕业了,成了作家了,儿子做了世上最成功的美容手术,儿子脱胎换骨逃离了“伤痕累累”的命,却不知母亲的脸父亲的腿都付之火海,变做“伤痕”!
无情的火!
突兀的火!
在商州的故事里,在红纸伞的传说里,总有这么多无情突兀的火。
为什么,我们从来就避不开这些火?!
为什么,我们总也躲不开这些劫难?!
为什么,烈焰和劫难会代代相传,永不间断?!
6。望断
老吴头静静地望着我。
他其实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他那双猎人独有的好眼力,没有放跑过任何一个掠过他视野的飞禽走兽,他怎么会认不出我?
“唉,唉,可惜呀!”老吴头连声叹息:“好人都这么命苦,那么啥人才有好命呐?好人都这么没有好报,那么啥人才有好报呐?”
我的心提到嗓子眼里了。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口干舌噪,头皮发紧,身上发冷。
终于,他说:“那个金丝猴一样的彤儿,偏偏也失踪了!”
“商彤!”我脱口而出:“我的弟弟——我的商彤,他——失踪了?!”
梦境中的樱桃谷,轰然坍塌。
梦境中的小木屋,轰然坍塌。
我似乎又看见十二岁的商彤,傻傻地对着我笑,随即,又被崩塌后的尘埃和火舌吞没。
我想说——我不相信我所面对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我愿它是梦。
我不相信在我目睹了尘叔的上吊,目睹了式微妈妈尼姑庵的佛堂前常跪不起的情景之后,在一场大火焚烧了一切灭绝了一切之后,命运依然这样残忍,竟又夺走我的弟弟。
可怜的商彤!
他的苦难开始于我少不更事时的一句妄言,而最终,也是我亲手斩段了我与他的手足情链。在我目睹了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苦乐变迁之后,在我因为读不懂人情世故而最终选择逃离之后,在我避开了一切烦恼之源落得个逍遥自在之后,我似乎从没有想过,是我把他推入了痛苦深渊,我就是那个从没有伸手拉他一把的——哥哥?!我曾为尘叔遗憾,为父亲和秋晓遗憾,为式微妈妈遗憾,更为了自己的过错遗憾,但我从没有想过,那个比我还要脆弱几百倍的商彤,该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勇气去面对比我更严峻的生活考验?
老吴头说:“你和彤儿长得真像,看到你,我以为就是他了,细想想又不是他了,他不会这么快就回来的,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老吴头告诉我,那一场奇怪的火灾,根本与商彤没有任何关联。着火的那天,他正好领着商彤到鸡公梁上围猎羚牛,夜宿在梁顶的山洞里。
老吴头告诉我,商彤十八岁那年参加工作,分在工程队,小小年纪就搬石运料,开山放炮,修筑公路。商彤就是在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失踪的,那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三年前?!
1992年?!
我被自己内心深处强烈的嘶喊吓着了。
三年前我在哪里?1992年我又在干些什么?
读完大学了?发表过作品了?存了一大笔钱又把它全用来做美容手术了?
沉淀在记忆长河中的几枚碎片悄悄地浮出水面。
我忽然想起,我曾经不止一次见过商彤。
我想起1992年秋季,我曾和一群同学做过一次远足。
我们来到秦岭之巅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碑上,再往前翻过几重山就是樱桃谷所在的那片林区。但我们没有继续前行,而是从另一条岔道上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