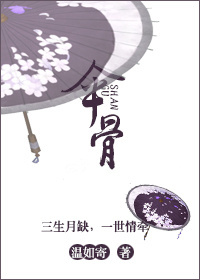红纸伞-第5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想起1992年秋季,我曾和一群同学做过一次远足。
我们来到秦岭之巅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碑上,再往前翻过几重山就是樱桃谷所在的那片林区。但我们没有继续前行,而是从另一条岔道上绕了过去。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正在修路的工程队,在急匆匆走过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一个穿劳动布工装的男孩,眉清目秀,长相酷似我的弟弟商彤。那男孩也朝我看了一眼,看得我心里发毛,脊梁发冷,膝盖发软,我几乎就要走过去招呼他了,却听见前边的同学喊我快走——那么恍惚,那么迷蒙,那么一个总在梦里出现的人,此刻却让我分不清楚是真是假,是虚是实——当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我面对着我的众多的同学,我竟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我好扭曲,好自卑,好担心别人的闲言碎语,好害怕给同学落下话柄,好害怕商彤会不认我,不理我,让我下不了台阶。
那一年我们都只有二十三岁。
1993年春天,我去上海做了整容手术,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欠下一屁股外债。
不过,手术的效果出奇的好,让我可以体体面面、轻轻松松地找到好几个打工赚钱的工作。
秋天的时候,我陪同一群中外记者去游览朱雀森林公园。
进入户县崂峪沟之后,有一段需要步行的便道,那个地方叫沙窝子,距山外的余下镇只有十几里地。有一支工程队正在那里施工,柏油沥青烧得昏天黑地,一塌糊涂,到处都是烟尘,我又一次看见了商彤。他正拿着铁锨,站在沙石绞拌机旁边,一双眼睛麻木而空洞地注视着我们这一群衣着花花绿绿的行人。蓦地,他看见了我,眼神一亮,愣了愣,呆了呆,脚步动了,疑疑惑惑向我走来。我又一次害怕了,退却了,逃避了——面对随行这一大批喜欢猎奇喜欢追逐和挖掘新闻事件的记者同仁,我怎能不害怕不退却不逃避?我怎敢去认这样一个弟弟?那一刻钟我满脑子都是自己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想到我终于走出了怎样扭曲怎样黑暗的生存环境才有了眼前这一点点成功——我连做了整容手术都不敢让人知道,我怎敢自己的隐私在一瞬间被曝光?我可不愿做焦点人物,不愿在媒介报刊上亮出家丑。我终于硬着头皮走过去了,走多远都不敢抬头,更不敢往回看。后来听旁边有人对我嘀咕:“商痕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有病啊,使劲儿跟着我们走,你看他和你长得还挺像的呐!”我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但在同时,我确实看见了商彤,他一直在跟着我们走。我们快他也快,我们慢了他也慢。我们绕过一座河湾,又翻过一座碎石山,还能看见他,愣愣地,拎着铁锨,一脸茫然。
后来我就去了大连,做了一年广告策划的工作。
在大连,我寻着了尘叔家的那栋小楼,找到了父亲年轻时呆过的那个话剧团——它已经拆迁,新地址是位于南石道街的一座刚竣工的文化大楼,很漂亮,很气派,很现代,练功房排练厅剧场应有尽有,可惜他不属于父亲;我为自己找的住处就在青云街,房子是快要动迁的老房子,租金很便宜,也很清静,建在绿山腰,屋后是疏密错落的松林,房前是一片色彩鲜艳的菜园子,视野很宽敞,不用走出房门就可看见那片母亲幼年时呆过的墓园,它就在山脚下,很荒凉的样子,已被世人遗忘。
199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构思关于墓园的小说了,稍有闲暇就去幕园里转悠——我在那里猜度母亲和尘叔的相识,想像着父亲的单相思和苦恋,晚上躺到冰冷的小床上我会彻夜失眠,或者在每一个难捱的长夜里恶梦连连。有一天我就梦见了商彤,他也在墓园里转悠,像我,像所有的亡灵,更像飘荡在残亘断碑间的孤魂野鬼,一片云雾缭绕之中,他追我在墓园无处可逃,无处可躲,追我到墓园外的绿山上,追我到悬崖峭壁的边缘,漫天鼓荡的寒风中到处都是他的声音:“哥哥,哥哥,为什么你看见了我却不敢认我?为什么我走近你,你却躲着我?”那些日子里,我总是被突如其来的梦吓醒——在梦中,我被商彤步步紧逼,却无从辩驳,后退无路,最后失足从悬崖顶上坠下去,坠下去。
1995年,由于喜欢《LOVE》,也由于我为《LOVE》写了《梨香院的故事》、《红璎珞》、《商州的家织布》、《商镇来了上海人》等诸多散文,以及《老区里的老妇联》,《走过战争的女人》等记者专稿,很被读者钟爱,也颇受主编青睐,我就回到了西安,来到了《LOVE》编辑部,做编采合一的工作。
4月份的时候,我去户县采访农民女画家李风兰,在马王镇换车的时候,我遇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她问我:“你认识商彤吗?”莫名其妙,我摇头。她又说:“你和商彤长得真像!”我坐上车后她又追了上来:“你一定认识商彤,你一定就是他的哥哥!”她说:“商彤曾对我讲过,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你一定是的。”汽车启动了,她追着汽车跑:“请告诉我商彤在哪里?我一直都在找他,我怎么也找不见,怎么也找不见他呀!”
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都不知道,汽车把她远远地甩开了,抛开了,但她一直在追着,嘴里不停地喊,不停地喊,喊!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只是,自此之后,我的心里会莫名发慌,莫名发痛。
那种紧牵着,揪扭着,直绷着的慌啊!
那种被窒息,被扯断,被掏空的痛啊!
让我不明白,商彤到底怎么啦?我到底怎么啦?
为什么,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会无所顾忌,我会心无旁怠地去喊他一声:弟弟。
为什么,在今天,我会有这么多的顾忌,我会做作,虚伪,冷酷,无情。
在我一次次做错事的时候,在我内疚、惭愧、自责、自怨的时候,在我对一切都无知无觉的时候,一定有什么发生了又被我错过了——维系着我和商彤的那根链子,似乎再也接不住了;或者,有一根线,蓦地断了,脆生生地响了一声就断了,我们谁也没有听见,却被各自的伤弄疼了,反弹向虚无,反弹向空落,反弹向缥缈,反弹向沉浮——什么时候他失去了我?什么时候我淡漠了他?我与他,竟然是无知无觉?无知无觉?!
老吴头告诉我,1992年秋天我在秦岭梁顶看到商彤的情景,商彤后来也对他说了。商彤那一刻的感觉挺像我的,分不清做梦还是清醒,分不清真实还是虚幻,他弄不明白那个背着旅行袋低着头急匆匆走过的披头散发的人,究竟是不是他的哥哥。
老吴头告诉我,1993年我在沙窝子看见商彤铺柏油路的情景,商彤也对他学了。商彤没料到哥哥做了整容手术,做了整容手术他更能一眼认出来这就是他的哥哥,他那时最想认哥哥。在我们一行人走远后,商彤在绝望中哭了很久。老吴头说:“细皮嫩肉的彤儿,天生就不是开山修路的材料,他每次回来都不愿再去工地,总要让你母亲好说歹说哄劝老半天才肯再去上班。”老吴头的声音幽幽地:“可怜的彤儿啊,他其实是想告诉你,你父亲的腿伤已转为骨癌晚期,你母亲被火烧伤的眼睛早已失明,他们都不久于人世了,他们想你啊,他们想你都想疯了,他想让你回去看看,回去看看。”
老吴头说不下去了。
让我觉得,日子一下子就过完了。
我在一瞬间,死了!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啊,让我先死吧!
不要给我太多羞愧,不要给我太多后悔,不要给我太多遗恨。
假若给了我这么多才让我去死,我一定会死不瞑目,我一定死得比谁都痛苦。
心里好害怕,好紧张,好惊惶!
也有所意识,我可能,我只能,我只有——也许可能——也许只能——也许只有——在天上——再见到他们啦。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是否,我已经是孤儿?
无爹,无娘,就是天涯的草呀,难道我真的?真的!真的已沦为孤儿?!
老吴头说:“可怜的彤儿啊,他看见哥哥不认他之后,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就直骂自己窝囊,没出息,一回家就发誓再也不去铺柏油路了。他看见你活得那么滋润那么有滋有味那么人前马后出尽风头,还指望你能帮帮他呐,给他在西安城里找一个临时工的活儿去干,也比干那开山放炮砸石头修路的要命的活儿强一些。他那么聪明,就不信在城里熬不出个人样儿来。”
老吴头的眼里冒出愠怒的火来:“好你个当哥哥的,你把你兄弟真给伤透了。”老吴头说:“回到家里不几天,你父亲就撇下他们娘儿俩个闭上眼睛,走喽!你母亲眼睛看不见东西,精神倒还刚强,可谁知,竟抗不过半个月,一先一后,他们竟都走喽,留下商彤,天可怜的,让人心疼的,让人心疼的,天可怜的!”
终于,知道了结果。
终于,沦为孤儿。
商彤和我。
我和商彤。
老天!
谁能还我父母的生命——哪怕是衰老的枯竭的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的爹娘,哪怕是山高水远、望穿双眼、苦思苦念、苦想苦盼的爹娘,也请还给我,让我重做儿子,做最乖的儿子;让他们重温旧梦,做最安详的旧梦。
谁能还我不是孤儿的命运——哪怕让我再经一万次苦难,也把父母健在的福份还给我,让我尽一天孝,让他们享一天福。
谁能还我樱桃谷的骨肉团聚——哪怕只有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轰雷掣电、火光电石——哪怕只有迅忽的瞬间!
谁能还我兄弟的笑容——哪怕这笑容重又化做利剑,戳穿了我的喉咙,刺进了我的心扉,割断了我的脉搏,剥离了我的生命。
谁能还我爱的权利——哪怕褪色了,流逝了,贬值了,哪怕被谁霸占了,哪怕被人用旧了。
也请还给我!
还给我!!
老吴头说:“一切都往坏处走——彤儿突然失踪了。临走前不言不传,交给我一个布包,说是父母留下来的,放在其它地方不安全,寄存在我这里他才放心。那一天是1993年的国庆节,他在我这里吃了早饭,说是去溪水坪镇子转一转,就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呀!!!”
老吴头说:“你知道吗?彤儿都快有媳妇啦!那个女娃子就像是天上的仙女似的,她在十八里苗圃上班的时候,彤儿也在那里修路,女孩儿是那么喜欢他,给他织毛衣衲鞋垫,天天做好吃的捎到他的工地,可他总是心不在焉的,好像压根就没那回事儿。屁股一拍,说走就走了,跟谁也不打招呼,女孩儿到处找他,到处找不见他,女孩儿好伤心哟,王宝钏一般的伤心哟!”
呵,想起来了,户县,马王镇,那个追车的女子。
商彤,我的好弟弟,我见过那个爱你的女孩子啦。
就在三个月以前的一天,在户县与长安交界的地方,在马王镇的汽车站里,那个女孩子说:“你认识商彤吗?请告诉我商彤在哪里?我怎么也找不见他!”
商彤,我的好弟弟,一世兄弟之后,我们就这样不再相见了吗?没来得及再说一句话,没来得及听你喊一声哥哥,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从没有忘记过你。血浓于水的手足情缘,怎么能说断就断?却为何,让我无法预知你的生死,无法更改你的命运——这些年,我们兄弟错过太多,也欠了太多——你欠我一声哥哥的呼唤,我欠你一世兄长的情份。
商彤,我的好弟弟!好弟弟!!好弟弟!!!
如果,我全部的人生就是这些失去;
如果,我所有的成长就是这些伤害;
如果现实真是这样——这样不可饶恕,不可挽回,不可拯救?
那么我的人生我的成长我的现实又是多么冷酷,苍白,虚无。
我在商彤面前所犯下又是多么大的错误?多么大的错误啊!
眼泪不可收拾。
就像天地间一场悲痛欲绝的雨,浇湿了脸,浇冷了心。
老吴头的声音在耳边想起:“哭吧,孩子,有多少眼泪都哭出来吧,哭完了,就回樱桃谷去,看看你的父亲再看看你的母亲,他们和你尘叔躺在一起了,三个苦命的人,三个寂寞的人,三个一生一世都不愿分开的人。”
老吴头交给我商彤留下的布包:“拿去吧,孩子,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你的兄弟。”
7。落山风
是啊,我该回樱桃谷去了。
我为什么不敢回去?
经历了如此严峻的生命打击,爱过,恨过,哭过,逃离过,绝望过,我该懂得去冷静思索——问世间,还有什么能让我把世俗的议论放在高于亲情的位置?
我可怜的父亲,比任何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刽子手都更多饱尝了苦果和报应,当他被生活的涡轮撞击得体无完肤的时候,对于他,我仍然只有爱。
我受难的母亲,比任何为情所困走不出情关的女子都命苦,当她终于乘鹤归去,我就只有无穷无尽的想念。
我的孪生兄弟商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不知道能否再见到他——这一刻,我只有祈祷苍灵,还我兄弟!
还有尘叔,撒手人寰十四载,年年岁岁寂寞如初,岁岁年年凄凉如故——尘叔坟前的草木若非已经成林?一堆白骨也许早已化做春泥,随烟散去。
呵,父亲,我回来了!
呵,母亲,我回来了!
商彤,尘叔,樱桃谷,我的亲人,我的天堂,我的诚挚如初的梦乡。
我回来了!
看我风姿绰约,天地飘萍,遗世而回。
看我摒弃了几多虚荣,又携来几多真纯?
看我依然年轻的笑靥里,有哪些是几经风寒依然执迷不悔的?
看我沧桑的灵魂中,有哪些是专门祭献给生命祭献给亲人?
在那些由成熟的信念和稚纯的热爱堆积起来的细腻思维里,清晰如昨地写着我在痉挛与惊蛰之后的所有想法——回归山林,回归樱桃谷,回归十四年前的自己——再做回那个十二岁的给父亲打酒喝的儿郎。
我的父亲,他在百米之外的地方看见了我。
我们隔着长长的十四年的空白,对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