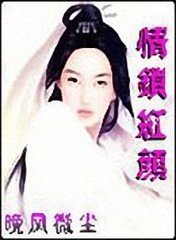桃花红-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里肉气氤氲,隐隐有俗世喜悦之意。周秋梨叫细细摆了九双碗筷,却只著她盛了两碗饭,跟细细说:「你去跟姊姊们说,家里常备她们的碗筷,她们要回来甚么时候都可以回来。我有甚么做得不对,我还是一家之主。」细细想,所有人都跑清光,他还在说甚么一家之主。也没答他,端起碗筷便吃。
饭酒过后,周秋梨脸红耳热,登起步子,唱起京戏来:「我楚霸王力拔山河气盖世。」嗓子还未拔高,便按著心脏,脸上由红而紫而蓝,呼吸急促,身体像虾一样蜷曲。细细飞快给他拿了心脏药,周秋梨已经无法吞咽,细细用手把药丸按进去,惊得牙齿一直格格作响,把周秋梨扶到床上便打电话叫救护车。周秋梨一直按著心脏,说:「很痛很痛很痛。呀──」叫到细细的骨头里面去,流了一脸的涎液和一床的小便。她没想到结局会这样猛烈。他一口一口的抽著气,破风琴似的,一只手紧紧的捉住了细细,把细细捏痛得眼泪都流出来。「放开,放开。」她说:「细细,细细,好可怕。」周秋梨断断续续的说。「放开。」周秋梨愈握愈紧,他一定想将她捏死。细细想起多年前与父亲游泳的那个黄昏。或许当时他将她的头按进水里,或许真想杀她,或许只想和她开玩笑,这个可怖的谜她一生都不会知晓。「放开。」她说。周秋梨只馀下几口气,他死了都可能这样捉著她。细细发起狠来,便用另一只手按住了周秋梨的嘴。
周秋梨放开了她。他停止了呼吸。
到底是她杀了他,还是他自然死亡,和他那个黄昏是否想杀她一样,都是一个她一生都不会开解的谜。
她坐著那里,空气还有残馀的肉香和酒香。细细低头看看自己,又是穿著一条吊脚睡裤,一双破拖鞋。她的父亲死了,她想穿好一点来送他终。
衣柜空荡荡的都是衣架,还有的便是一套她刚洗乾净的校服。她便换上了校服,穿上上学的鞋子,端端正正的坐在她父亲身旁,等人来收尸。
后来她记得那天她下课便到医院认尸。医护人员力称是她报的警,当时病人经已死亡,细细经已全记不起来。
从那时开始细细记性便很差,连到殡仪馆都摸错地方,万国殡仪她记得是香港殡仪,害得她每层每间的去找,待她搅清楚地方又得摸过海去,过海隧道又惯常的塞车,她到殡仪馆时他们已经走清光,殡仪馆在关门,她在纷杂的花堆里徘徊了好一阵,想乘隧道巴士回西环的家,大概走错了方向,在车上迷迷糊糊的睡了,醒来车上只剩下她一人,下得车来,凉风阵阵,原来去了沙田,又来来回回的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家,她老觉得,永远在寻寻觅觅,永远回不了家。
因为专注於解释事物的客观规律,细细的生活总是十分糊涂,成了一般人口中的「艺术型科学家」,将手表当作鸡蛋放进热水煮那种。细细熟悉质子分裂的速度,光的折射途径,硫磺氢炭氯氮氨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却可以考试忘记带准考证,袜子只穿一只而忘记另一只,出门忘记关水喉经已4次,每次屋子都是淹得几乎可以养鱼,细青大吵了好一阵细细索性自己在离岛租间小房子,读书考试,入大学念工程后搬进宿舍连过春节都不肯回细青的家睡,每次回到细青处都热水烫脚的赶这赶那,细青嘲她「旋风式到访」。现已杯盘狼藉,细青细月都喝得满脸通红,细细挂念无人宿舍的冷静,长长的走廊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她案头电脑绵延的电流声,便轻轻说:「我想我还是先走了。」细凉「嗖」的一声止着她:「你这时叫走大姊少不免会哭闹一顿,还是耽一会吧。」细容听到了,便低低道:「你要走不如悄悄的走,我看大姊还是大哭一顿收场。我们都走吧。」尽管麻将声啪啪响,细青听得一个「走」字,便麻将都不打了,跳了起来:「谁要走了,这夜不是团年夜吧,谁要走了,你们都看不起我,都要走了。爸爸死后,你们都当我死了,我死了倒好。」细容便拉着她:「怎么了,大家开开心心的,你又何必伤感。」细青听得「伤感」两个字,才觉得伤感,便呜呜的哭了起来,细月也过去搂着她:「姊姊,这不好。赵得人是客人,你让客人难做有甚么好呢。」细青益发哭得厉害了:「你要结婚了,我还要自己一个人。」细容笑:「你如果肯我给你介绍人好不好?」细青哭得一脸都是泪:「现在我是甚么了,我都要你们给我介绍人,我竟沦落至此了。」赵得人站在那里,实在插不上话,见细青及姊妹们你一口我一语,却任由细青眼泪鼻涕的直流,便给细青递上了自己的手帕。细青接过来,深深吸一口手帕遗留的古龙水香气,问赵得人:「你是不是同性恋的?这么好。」惹得众姊妹都笑了。又问赵得人:「你觉得我们家姊妹怎样?」吓得赵得人满脸赤红,嗫嚅道:「没怎么样,很……很……很没怎样。」细月笑:「你到底说甚么。」此时细眉掩上眼,道:「好黑。」然后「拍」的一声,客厅便陷入黑暗之中。细凉哇哇的叫起来,细玉在黑暗中道:「这是个黑暗的大年夜。你看,整个城市都黑了。」细月在漆黑中握住赵得人的手:「停电了。」细眉说:「黑暗里有光。好光。」细凉便拉尽了窗帘:「失火了。或许因为停电,所以失火」姊姊妹妹便围在窗前看失火。赵得人方知原来夜里的火是这样的美丽热烈。失火的大概是近摩星岭的木屋房子,橙黄的烈焰吃进沉绿的山里去,喜欢跳跃,如狂欢节。救火车和救护车划着鲜红明蓝的闪光,呜呜的前进,时而停顿,有片刻的寂静,或许有点人声,不过无法听清楚,那或许是个懒惰的父或母,第一次情深的叫唤他们的子女,不过他们可能已经葬在烈焰之中了。姊妹们紧紧的搂着,以火以死,她们才相互绻恋。赵得人站在她们背后,说:「我知道怎样形容了。你们姊妹就像活在烈火中一样。」细凉道:「这你是自视为救火车了。」赵得人道:「不敢不敢,实在是杯水车薪,能自救就差不多了。」细玉道:「好吧好吧,你请我们喝酒,以酒当水吧。」便摸黑去点蜡烛。细眉不知从那里找到了好几十支白烛,借点摇动的烛光,一支一支的截断,在窗台上,桌子上,椅背上,地上,点了一支一支的小蜡烛。细玉开了赵得人带来的圣安美莉安红酒,给赵得人及众姊妹倒了半杯,酒就倒空了,细眉在她身后叫她:「玉姊姊,人老了是不是会像河马。」细玉一震便推翻了酒瓶,碎了一地的绿玻璃。细眉道:「你们会受伤的。」细月已经一脚踏在玻璃碎上,她没有穿鞋子,脚底流了一行基督钉十架一样殷红的血。细容跪下来想拾玻璃,膝头又嵌进了绿宝石般的碎片。细凉叫她们勿动,去厨房找药箱,回来时一脚踏在洋烛上,烧得痛,跳开时跳到绿晶莹上,又流了血。细眉弯下身来,左手擎着烛,处女新娘一样静默专注,为她们拔出碎片,然后在地上摸索,一一将碎片拾起,灰黄的柚木地板已散布了一滴一滴的血。细眉蘸了血,舐了舐,道:「血是甜的,酒是涩的,而水是无味的。」站起来,左手依然提着烛,右手拿起杯,大口大口的喝着水。赵得人想起他中学时代念的圣经,忽然明白过来:以血救赎,以酒解忧,以水洁净。各人流各人的血,各人寻得各人的救赎。毕竟彻悟并不容易。这一夜,血酒水都有了,算是人生的得着。他不知道如何对细月说清楚,只道:「我想我今夜……。」细青按着他的唇,说:「别说话。」原来细青已经伏在地毯上睡了,囡囡在她身旁打鼾,此起彼落的,细青喃喃的说梦话:「窗关好了没有,要下雨了,我要给妹妹们买雨衣。」众姊妹演员退场似的,轻手轻脚的在收拾。 细月买来的那株桃花,盛夜黑暗之中,忽然开放,或许因此会忽然堕落。
细容站在桃花之下,有点恍惚。
这么多年了。细青执於她自以为的爱。永不可得的爱。超越道德的爱。因其如此,她和所有姊妹都不一样。
细青梦见了桃花不停在流血,她站在花枝下,不得不打伞。
「窗关好了没有,要下雨了。」她说。
她要给妹妹们买雨衣 。唯独不给细容买。
「这么多年了,你还执迷不悟,细青。」细青听得细容说。她听不清楚下一句是甚么,想靠近一点,细容却一点一点的退后,然后,飞走了。
「细容,细容。」她一叫,便醒来了,很想张开双眼,可惜眼皮并不听使唤,想扬手,手却不知那儿去了,想开口,却无法说话。
「我一定在作梦。」细青想。
细容正在穿大衣,戴一双夜绿色手套,抹了抹嘴,想补点玫瑰野露口红,隐隐听到细青叫自己的名字,看看,她还伏在地毡上,细玉给她盖了薄毛毡。她便对着小镜涂口红,在镜里看到了细青。
她打开了皮包,掏出了支票簿 ,给细青签了一张支票。
细月已经穿好了短夹克,见到细青在签支票,便止着她:「我来,我来。你把钱省下了给囡囡买点好东西。你在外靠救济金,环境也不会十分好。」便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现金来。细玉瞠目结舌,细月苦笑道:「我愈来愈像黑社会。没办法,他们都这样。」细凉笑道:「我以为你已经是黑社会。」细细已经穿戴整齐,忽然眼前一亮,电灯一一亮着,细青转一个身,手上握了一朵刚落的桃花,掩着了脸。细细吹熄了白洋烛,便脱下大毛衣:「今天晚上我还是不走了,我看一看她。」细容道:「乖孩子。或许应该留下的是我。」囡囡一直在打呵欠:「妈妈,走吧走吧。我们回舅舅家睡吧。」细月便将两叠现金塞给细细:「厚的给大姊,薄的给你,可不要弄乱了。」细细将客厅大灯关掉,以馀饭厅的一盏吊灯,照着一桌子凌落的碗筷,散落的麻将牌、水果皮、瓜子壳、空酒瓶、茶叶、莹绿的玻璃碎,一滴一滴,枯乾的血迹。细眉走到垃圾堆里,找着她的羊毛袜,站在那里,半明不暗的在编织。赵得人觉得有点湿湿的,抬头看,大年夜竟然下起牛毛细雨来,街灯份外的橙黄,火烧似的,远处的火经已熄灭。 夜深赵得人觉得前所未有的清醒。他忽然记起一个意大利神父的脸孔。那是张安详而清醒的脸孔。关於阿都诺神父,有人说他是个没落贵族之后,有人说他是个同性恋者,有人说他「躲进了修道院」,为了甚么,不得而知。他教的是数学,上课却给他们讲苏格拉底之死。他们发现阿都诺神父在垃圾桶里那一年赵得人念中五。他们围住了垃圾桶,说阿都诺神父死了,没有表面伤痕,可能是自然死亡。赵得人站在人群的外圈,挤不进去也没打算挤进去,站在修道院校园的草地上,赵得人突然觉得很清醒。 如今他想他明白。「躲进修道院里去。」各人或以血以酒以水,寻求各人的救赎。
在修道院里,躲无可躲,所以躲进了垃圾桶。
但救赎就在眼前。
细月在他身旁睡了,胸脯微微起伏,如同鸽子。汽车在公路上静静奔驰。他握著驾驶盘,却伸手握住了细月的手。在幻灭的不惑之年,他们能够遇上对方,又能够发生感情,是生命给予的福惠。细月的过往是他无所知甚至不愿知,他知道的只是眼前的女子,他并愿意包容与接纳,一切关於她的,创伤与骄傲。她这时只是非常疲倦的睡了。雨愈加的大了,密得近乎紫色。他只是听得雨的落下,非常静,静得整个世界都要塌下来。再看细月,她流了一脸的眼泪,双眼仍然紧紧的闭著。他摇了摇她,问:「怎么了。」她方缓缓的张开眼,道:「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父亲要杀我。」赵得人伸手摸她的脸:「不会的。你父亲已经死了。」细月含含糊糊的道:「是呵。」又沉沉的睡去。赵得人掏手帕来替细月抹乾了眼泪,然后用手帕掩住自己的嘴。泪的气味,微酸,勾起婴孩记忆,但细月的身体又明明散发成年女子的脂粉与汗香。赵得人才想起,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细月的眼泪。这样她就是他的妻子:他看到了她从不让人看见的。 这时漫天的雨,由紫而红,夜里像也有彩虹,慢慢的淡化,愈来愈轻,赵得人以为是下著粉红的雪,揉揉眼睛,满目满怀,都是堕落的桃花。他加快油门,开进桃花雨里去,落红纷纷,不过是过目急景,过了便天蓝海绿。他一直开一直开,愈开愈漆黑,开到无色无声的混沌去,黑暗尽处,有光。他开到微亮之处,彷佛有桃,但已经长了绿叶,亭亭如盖,花不过是记忆。他想景色至此,真是好,眼前豁然开朗,无夜无色,一夜风和雨,就此收尽。 细青就在这时醒过来,如此这般,由血肉相连的痛楚,想起了七姊妹。